
新近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推出的增訂重編本《夏鼐文集》(五冊),囊括了夏鼐在1930年至1985年的半個多世紀,從早年治中國近代史到攻讀埃及考古學🦵🏿,再到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中國考古學的許多領域,如此博大精深,令人嘆為觀止。但是🧑🏼🏫🫅,夏鼐對中國考古學發展的巨大貢獻,絕不限於他本人的一系列論著,更重要的是他身體力行地倡導中國考古學界謹嚴的治學風尚🧋🎋。夏鼐對考古研究成果的公布要求得極為嚴格👨🏽🚒。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考古所編輯出版的數十種考古報告和專著🤘🏽🆙,大都在發稿前經他審閱;《考古學報》和《考古》雜誌的重點文稿🈳、外文目錄和提要,也都在出版前經他審定。大到學術觀點的審核🚙,小到文字、標點和圖表的校正,引用文獻的核對,他無不密切關註➖。中國考古學書刊在國際上長期保持高質量的聲譽,是與夏鼐的嚴格把關分不開的🤝👰🏼,凝聚著他無私奉獻的大量心血😠。而夏鼐歷年主持編撰的中國最早幾部綜合性考古學論著,從1960年代初的《新中國的考古收獲》🤷♂️,到1980年代中期的《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則體現了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從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歷史進程💡,在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具有裏程碑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前,考古工作基礎薄弱🎑,田野考古人員極少😱,沒有自著的通論性著作。1950年代初🧏🏿♂️,全國有限的田野考古人員中,只有兩位先生留學外國、熟悉先進國家考古研究狀況。梁思永臥病多年、身體極度虛弱,夏鼐是唯一受過科班訓練、能夠親臨第一線的專家🫲。因此,培養田野考古骨幹人才,指導考古研究的重任,便歷史地落在他的肩上。夏鼐連年為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以及全國考古訓練班,親自講授考古學通論和田野考古方法,手把手傳授考古發掘的理念與技能🧑🦯➡️,從而成為考古學界公認的一代導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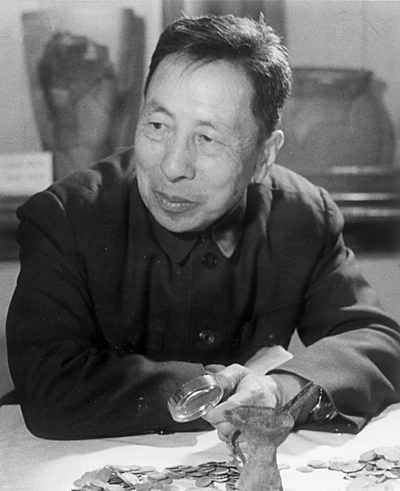
夏鼐
夏鼐主持國家考古研究機構三十余年,為推進中國考古學的全面發展和學科體系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堅持考古研究的基礎是田野工作😄,註重考古發掘的科學水平🛺,切忌“挖寶”思想;親臨現場進行具體指導🆕,認真審閱考古報告😈。他又及時總結各地考古工作的收獲,並在關鍵時刻撥亂反正,引導大家明確學科發展方向🧑🏿🏭,避免誤入歧途,因而被譽為中國考古學界的引路人和掌舵者📣。而他個人在百忙之中進行的學術研究,則具有學識淵博、視野廣闊、治學謹嚴的特點🚣🏼♀️,在考古研究的許多領域都有傑出的成就🖨。
對中國史前考古學進行創造性的研究
夏鼐對中國史前考古學進行了長時間的創造性研究。主要是最早根據可靠的發掘資料,改訂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編年體系,規範考古學上的文化命名💆🏽;最早提出中國新石器文化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統🧑🦲,並在現階段倡導從考古學上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
1940年代🥾,夏鼐在已有學者對安特生(J.G.Andersson)主觀構擬的中華遠古文化分期提出質疑的情況下,第一次通過甘肅地區的調查發掘🔋,改訂齊家文化與甘肅仰韶文化(即馬家窯文化)的相對年代,提出中國史前時期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統🦋,從而宣告曾有相當影響的安特生分期體系的徹底破產♓️,標誌著中國史前時期考古研究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田野考古在全國展開⚧,許多地方發現前所未知的新石器遺存🤴🏼,過去習用的幾種文化名稱已經難以概括🛩。面對日趨復雜的情況,如何正確進行新的文化區分和命名,成為考古研究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夏鼐於1959年年初及時發表《關於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一文💪🏼,對什麽是考古學文化、劃分考古學文化的標準,以及定名的條件和方法等問題,給予科學的回答🪱。該文指出,考古學上的“文化”是指某一社會(尤其是原始社會)的文化在物質方面遺留下來可供觀察的一群東西的總稱,用以表示考古遺跡中所反映的共同體🧎🏻➡️,通常以第一次發現典型遺跡的小地名來命名。而確定新的“文化”名稱,需要具備三個條件:(1)必須是有一群具有明確特征的類型品。這種類型品,經常地共同伴出,而不是孤獨的一種東西;(2)這種共同伴出的類型品,最好發現不止一處;(3)必須對這一文化的內容有相當充分的認識,至少有一處遺址或墓地做過比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夏鼐的基本態度是從實際出發,慎重處理👩🏼🦲,既不要遲疑不決👐🏿,以致不同類型的文化遺存長時間的混淆在一起🚴♂️,延緩研究工作的進度;又不要輕率浮誇,看到某些片面的個別現象🧑💻,就匆忙地給它一個新的名稱🏄🏼,造成一些不應有的糾紛👨🏿🎤。他還預見到,區分考古學文化時,對“哪些可以算是兩個不同的文化,哪些只是由於地區或時代關系而形成的一個文化的兩個分支”,即在考古研究中如何界定文化、類型和分期的問題,學者之間會有不同看法🙋🏻,需要留待將來再作詳細討論,啟發大家更加深入地思考問題🧑🏿🔧。這篇文章,統一了中國考古學界對文化命名問題的認識,從而推進考古研究的健康發展,尤其是對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分布👨👩👧、類型劃分和分期問題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使之出現新的局面。
夏鼐對中國史前考古學的又一重大貢獻🧔♀️,是“文革”前夕在他的領導下建成了中國第一個碳十四測年實驗室。1977年,他發表《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一文,根據當時公布的各種史前文化的年代數據,結合文化內涵和地層證據,全面討論它們之間的年代序列和相互關系,亦即中國史前文化的譜系問題♞。該文提出許多富有啟發意義的獨到看法🎣,尤其可貴的是,更加明確地提出中國新石器文化的發展並非黃河流域一個中心的多元說。該文指出,所謂文化類型的不同🙆🏼♂️,“表明它們有不同的來源和發展過程,是與當地的地理環境適應而產生和發展的一種或一些文化。”又說☂️:“當然這並不排除與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有互相影響🥤,交光互影。這種看法似乎比那種一切都歸於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響的片面性的傳播論,更切合於當時的實際情況,更能說明問題。”中國遠古文化的發展🦄,從傳統的黃河流域一元說改變為並非一個中心的多元說,這是中國史前時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此後四十年來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使多元說進一步確立,成為眾多考古學家的共識。社科院考古所在夏鼐的領導下,有重點地開展黃河中下遊😟、長江中遊和鄰近地區的新石器時代田野考古⛵️,則為中國史前考古學打下堅實的基礎。
隨著有關考古資料的日益豐富🪇,夏鼐又於1983年提出從考古學上探討中國文明起源——這一中國史前考古學和世界文化史上至關重要的課題,強調其理論意義在於“傳播論派和獨立演化派的爭論的交鋒點”。他從明確基本概念入手,強調“文明”一詞是“指一個社會已由氏族製度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夏鼐認為🪬,根據現有考古資料,不僅深刻地認識到殷墟文化是高度發達的文明,更重要的是從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二裏岡文化和更古老的二裏頭文化,三者互相聯系🛟、一脈相承;而二裏頭文化,至少它的晚期既夠得上文明,又有中國文明的一些特征,如果不是中國文明的開始💂🏽🌍,也是接近於開始點了;至於比二裏頭文化更早的各種文化,都屬於中國的史前時期🏊♀️。
夏鼐還特地討論中國文明是否獨立地發展起來的問題🛃,著重分析那些與中國文明起源問題關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主要是中原地區👩🏼🦲、黃河下遊和長江下遊的晚期新石器文化🤷🏻♂️,斷定“中國文明的產生,主要是由於本身的發展。”他說🤴:“中國雖然並不是完全同外界隔離😪,但是中國文明還是在中國土地上土生土長的🧝🏼。中國文明有它的個性,它的特殊風格和特征👮🏽♀️。”他還曾講到,進行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主要對象是新石器時代末期和銅石並用時代的各種文明要素的起源和發展,例如青銅冶鑄技術、文字的發明和改進♢、城市和國家的起源等等”👷🏿,同時又強調“文明的誕生是一種質變,一種飛躍”。這便為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探索指明了方向,從而導致此後有關研究和討論長盛不衰🤴🏿🧙🏽♀️,不斷深入,乃至本世紀初開始進行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的縝密探討
夏鼐說過〽️,考古研究進入“歷史時期”,便要掌握狹義歷史學中的大量文獻和運用文獻考據功夫。他在歷史考古學方面的一系列論著,突出地反映其文獻根底深厚,擅長歷史考據,善於從豐富的考古資料出發🧑🏻🦼,結合可靠的文獻記載↗️,不斷進行新的探討。特別是從方法論上給人啟示🤦♂️🕹,引導大家正確地對待文獻資料,深入細致地進行研究。

1984年,夏鼐(右)與英國李約瑟博士在一起。資料圖片
1950年代末,當夏文化問題探索剛著手的時候,夏鼐就曾指出👩🏿🎤,應該審慎地對待“古史傳說”資料,其中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傳的真正傳說🥂,又有先秦諸子編造的歷史哲學。1977年有關單位發掘登封王城崗遺址以後,一些人認為王城崗遺址可能是“禹都陽城”,夏文化問題已經解決。夏鼐針對眾說紛紜中的糊塗觀念♟,又從基本概念上進行澄清。他指出,“夏文化”應是夏王朝時期的夏民族文化,因而在研究中需要分辨不同的時期、地區和族系。又說🧑🦳,夏文化問題在年代學上很麻煩,商年和夏年都有懸殊較大的不同說法,目前並沒有弄清楚;夏都的地理位置也很麻煩,“禹都陽城”說出自上距夏禹兩千年的《孟子》🫅🏻,另外還有禹都安邑的說法;縱使“禹都陽城”可信,它和東周陽城是否一地仍需證實🏖。這種周密思考😼、認真分析的科學態度,推動了夏文化探索工作的發展,使有關研究不斷深入🫨。
根據夏鼐的學術思想,社科院考古所對於歷史時期考古,著重於歷代都城遺址的勘察發掘,兼及新疆、內蒙古等邊疆地區,以及若幹手工業遺址的考古工作🧆,持續進行🧒,逐步深入🎱,取得顯著的成績。
夏鼐對於古代器物的研究,例如商代和漢代玉器的研究,則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首先,註意探討中國古玉的質料和原料產地,提倡對各地出土的玉器多作科學鑒定,從礦物學上判別它們的顯微結構和所含元素,以便與地質礦產資料比較分析。其次,強調正確判定玉器的類別、名稱和用途,不能繼續采取傳統的“詁經”方法,而應改變為謹慎的考古學方法🪙,即根據各種玉器的出土情況,以及它們的形狀⌨️,結合傳世品和文獻資料考證其古名,用途不明的暫時存疑。由此他斷然判定,“所謂璿璣不會是天文儀器”。這便為中國古代玉器的研究開辟了新途徑,使古玉研究從禮學家煩瑣考證的窠臼中解放出來,對歷史考古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開拓中國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學研究
1950年代初,夏鼐在河南輝縣第一次親手成功發掘出古代木車痕跡🧈,並根據輝縣戰國車馬坑和長沙漢代車船模型,進行古代交通工具的復原研究👨🏻🦲。1960年代起,他則根據考古資料,深入探討中國科技史上天文、紡織、冶金等方面的光輝成就⛄️。
關於天文方面,夏鼐主要是對幾幅有代表性的古代星圖進行了研究。他曾精辟地指出,中國古代的星圖有兩類:一類是天文學家所用的星圖♞🧑🍼,它是根據恒星觀測繪出天空中各星座的位置,一般繪製得比較準確,反映的天象也比較完整;另一類是為宗教目的而作的象征天空的星圖和為裝飾用的個別星座的星圖🧑🏿🏫。經夏鼐詳細考察後發現➝,後一類有現已發現年代最早的洛陽西漢壁畫墓星圖,以及最早表現黃道十二宮的宣化遼墓星圖🤲🏻🧶;前一類有現存年代最早的唐代敦煌星圖。
洛陽西漢壁畫墓星圖發現以後,曾有學者對比現代星圖進行解釋,由於不了解中國古代天文學和西洋天文學的差異,所作解釋多有不當。夏鼐從辨明正確的研究方法入手🐲,提出:(1)這星圖的內容👡,並不是比較全面地表現北天的星圖👩🦼➡️,僅僅是選用少數幾個星座,因而只能用中國古代星座對照,不應用西洋星座對照;(2)這星圖是西漢末年的😧,應該以《史記·天官書》作為主要的對比材料,而以《晉書·天文誌》所載作為補充🎃;(3)比較不能漫無邊際,首先應註意的是北天亮星的幾個星座和天球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宿,它們可能是古人繪製星圖時用以選擇的主要對象。經過這樣重新比較🫅🏿,確認該星圖既不是以十二個星座來表示十二次🥜💯,更不是象征十二辰,只是從漢代天官家所區分的“五宮”中每“宮”選取幾個星座用以代表天體而已。
夏鼐關於宣化遼墓星圖的論文🕍,根據遼墓壁畫中的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圖像,結合大量文獻資料🙁,進一步論證了中國古代天文學體系的特點,指出以赤道為準的二十八宿顯然是起源於中國,後來由中國傳至印度的,而黃道二十宮則是隨著佛經的翻譯由印度傳入中國。至於中國二十八宿創立的年代,他認為“由可靠的文獻上所載的天文現象來推算📐,中國二十八宿成為體系👩🚀,可以上溯到公元前7世紀左右🌃。真正的起源可能稍早,但現下沒有可靠的證據。至於文獻學方面的考據結果𓀛,也和它大致相符而稍為晚近🌞,現下只能上溯到戰國中期(公元前4世紀)而已”🧔🏻🍐。夏鼐的意見,被公認為中國天文學史研究中對於二十八宿創立年代這個聚訟紛紜問題的較為穩妥的看法。
關於敦煌寫本中的兩件唐代星圖,夏鼐將現存英國不列顛圖書館的一件稱為甲本,現存敦煌市文化館的一件殘卷稱為乙本。他判定兩本的抄寫年代,甲本在唐代開元👨🏿🔬👦、天寶年間(公元8世紀)👩🏽🦰,比英國李約瑟博士判定為後晉天福年間(公元10世紀)👩🏽🦲🧑🏻🦯➡️,提早了200年🏜;乙本在晚唐至五代時期(公元10世紀),則是第一次進行如此深入的研究。
夏鼐又是中國學術界根據考古資料進行紡織史研究的先驅。早在1920年代🐮,西方學者即已進行新疆出土漢代絲織品的研究🧑🏻🏫。1961年至1962年🤹♀️,夏鼐通過新疆民豐、吐魯番兩地新發現的漢唐絲織品的若幹殘片和原大照片👏🏿,參考過去其他地方出土的有關資料,考察漢唐時代綺🤷🏿♀️、錦和刺繡的紡織工藝與圖案紋樣🚵,附帶討論中西交通史上的問題💵。1972年💮,他又發表《中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一文,第一次根據考古資料系統論述漢代和漢代以前養蠶、植桑、繅絲和織綢方面的發展情況,並對漢代織機進行新的復原〽️,以進一步闡明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對人類文明的這一偉大貢獻。
夏鼐指出,發明蠶絲生產技術的確切年代🙏🏻,目前雖然還無法確定,但中國在上古時期是唯一掌握這種技術的國家🙎🏻,至遲在殷商時代已經充分利用蠶絲的優點,改進了織機,能夠織成精美的絲綢🙄,遺存實物有普通平紋🌍、畦紋和文綺三種織法。他表示,中國當時除使用豎機外,可能也使用平放或斜臥的織機,這便和古代希臘、羅馬等國家專門使用豎機不同👨🏻🦯👩🏿🌾,可能改進到使用吊綜提花和腳踏👭。東周時期已有織錦機🧒🏼。他又指出,中國的絲織生產發展到漢代至少已有一千多年歷史⚫️,達到了一個高峰🕎。五彩繽紛的漢錦代表漢代織物的最高水平,一般是使用二色或三色的組織法,如果需要四色或四色以上,便需要采用分區的方法,在同一區內一般都在四色以下。至於漢代的織機,根據實踐經驗和認真分析,他指出有些學者所復原的織機“是不能工作的”🫳,遂以江蘇銅山縣洪樓村出土畫像石中的織機圖為主要依據,經過多次討論➰、反復試驗和修改,重新作出比較合理的復原👷🏼♀️。他還發現,漢代畫像石上的織機都是簡單的織機,但漢代的考古發現已有錦🚽、綺、文羅等提花織物,至於如何製織有待探討。
在進行新疆出土絲織品研究時😊,夏鼐曾連日伏在燈下,用幾色絲線試作編織,以揣摩漢錦的織造方法,然後再用鉛筆繪出織物結構的草圖🈁🧆,即通過自己的實踐⛄️🏷,摸索進行古代絲織品工藝考察的途徑🔻。1972年,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發掘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絲織衣物🧙🏻♀️,有關部門委托上海的紡織科研人員對此進行工藝考察👩🔧🤱。科研人員不曾接觸過古代絲織標本🔐,首先閱讀的就是夏鼐的論著,以此啟蒙,然後再著手馬王堆絲織品織造工藝的研究。
夏鼐對中國的冶金史研究🫁,也有突出的貢獻。1972年河北槁城臺西村商代遺址出土一件鐵刃銅鉞,初步的技術鑒定以為鐵刃屬古代熟鐵🤰🏼。這項發現如果屬實,將是中國科技史上的重大發現👨🏼🎤,表明我國先民早在公元前14世紀已經開始人工冶煉熟鐵⛴🌮,因而迅速得到夏鼐的高度重視🎲。他考慮到人類在發明煉鐵以前往往利用隕鐵製器👨❤️👨,而鑒定結果中鐵刃的含鎳量高於一般冶煉的熟鐵,當即表示鑒定並未排除這具鐵刃實為隕鐵製品的可能,因而尚需作更加縝密的科學鑒定。後經鋼鐵專家柯俊教授重新組織鑒定,多種現代化手段的分析結果確認🪃,槁城銅鉞的鐵刃不是人工冶煉的熟鐵,而是用隕鐵鍛成的,從而避免了由於不慎誤判而在國際學術界造成惡劣影響🧑🏫。
夏鼐對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學研究🖖🏽,也有開拓之功。他最早對我國各地出土的波斯薩珊朝文物進行研究🫃,例如對新疆、青海🦛、西安🧔🏼♀️、洛陽和定縣等地出土的銀幣,大同、西安等地出土的金銀器皿🌸,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織錦,都曾撰寫專文進行考察👩🦼➡️。在逐項具體研究的基礎上𓀂,他又發表綜論文章,進一步探討中國和伊朗兩國友好往來的歷史,對中西交通的路線提出創見。
夏鼐根據一些地方發現的薩珊式金銀器和織錦,深入討論了波斯文物在中國的流傳及其深刻影響。他指出🫅🏿,這些器物在唐朝初期輸入更多,並有中國的金銀匠人模仿製作👰🏽,可能也有波斯匠人在中國製造的。薩珊帝國覆滅以後👨🏿🎓,直到安史之亂🚴🏿♀️,仍有這種金銀器的輸入或仿製。中國製造的仿製品😺,一般器形和波斯所製大致相同👏,但花紋常是唐代風格⏸。而瓷器🫛🏊🏼♀️、漆器和銅器中,也有模仿薩珊式金銀器的情形。
夏鼐還最早對北朝、隋唐墓葬出土的東羅馬和阿拉伯金幣進行過研究🧎🏻♂️。對海上絲綢之路和外銷瓷問題,也有論述。
王世民🫸🏿,1935年生,江蘇徐州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195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進入考古研究所後,長期從事秘書工作,參與多種大型集體編撰項目🪲,致力於中國考古學史和商周銅器研究🧜,主編《夏鼐文集》《夏鼐日記》等。
學人小傳
夏鼐,字作銘👨🏽🔬,1910年2月7日出生在浙江溫州一個經營絲綢業的商人家庭🧜🏻♀️,少年時代曾在上海光華附中刊物上發表與呂思勉教授商榷的文章🏌🏼🤧,對“茹毛”指“食鳥獸之毛”的傳統說法提出質疑。1930年考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後考入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二年級插班,師從陳寅恪、錢穆、蔣廷黻等名師👋🏼,致力於中國近代史研究,開始在史學領域嶄露頭角。1934年以“名列榜首”的成績考取留美公費生的考古學名額,在傅斯年、李濟兩位權威的指導下進行業務準備,並以實習生身份前往安陽殷墟,參加梁思永主持的殷代王陵區發掘🥡,走上以田野考古為終身事業的治學之路。
1935年夏🔟,夏鼐經有關方面同意🧹🥴,改赴英國留學,參與惠勒(M.Wheeler)教授主持的梅登堡(Maiden Casrle)山城遺址發掘,經受田野考古科班訓練。又曾在去埃及、巴勒斯坦發掘後🔜🤲🏻,謁見埃及考古學泰鬥彼特利(W.F.Petrie)爵士🧑🏼⚕️📩,得到這位大師的直接教誨。夏鼐主攻埃及考古學,師從埃及學權威伽丁內爾(A.H.Gardiner)教授,學習古埃及象形文字;在格蘭維爾(S.Glanville)教授指導下,對古代埃及的各種串飾進行系統的類型學研究💪🏿,成為中國第一位埃及考古學家👨🏿🚀,1946年他被授予博士學位🫃。他的學位論文《古代埃及的串飾》,至今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近年已正式出版(中譯本不久也將出版)。1941年初,夏鼐回到抗日烽火中的祖國後方,先後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1944年~1945年,與北京大學向達教授共同率領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前往甘肅敦煌和河西走廊進行艱苦的考察,取得中國史前考古和漢唐考古方面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1947年晉升研究員,並曾受托代理史語所所長職務🧔🏼,由此奠定其在歷史考古學界的地位。
新中國成立後,夏鼐歷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考古所名譽所長,中國考古學會首任理事長等職,領導國家考古研究中心機構三十余年🧑🎓,致力於考古工作隊伍的建設和實事求是優良學風的形成🖐🧍🏻,考古研究規劃的製定和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學方法的應用和多種學科研究的協作🩰,以及與外國考古學界的交流,極大地推進中國考古學全面的健康發展。
由於夏鼐傑出的學術成就,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重視。他早在1955年即以中國田野考古權威的身份👨🏿⚕️👩🏻🎓,榮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74年起📁,先後被英國學術院、瑞典皇家文學歷史考古科學院🏹、美國全國科學院等六個外國國家學術機構授予通訊院士(或外籍院士),成為我國學術界接受外國榮譽學術稱號最多的學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