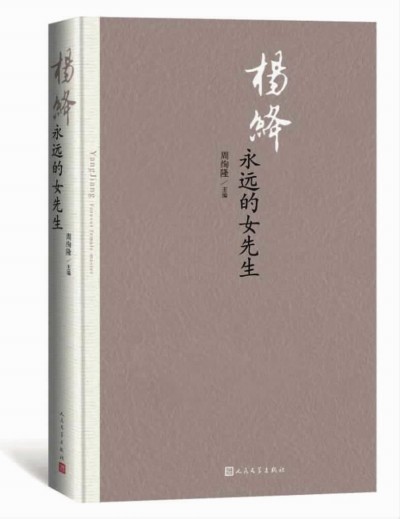
“老”與“死”是不同的,“病是外加的,臨時性的,不論久病、多病,可以治愈🈷️🗡。‘老’卻是自身的,是生命日漸萎弱🧑💼,以至熄滅🥞🙍🏿♂️。老人就是dying的人,慢吞吞,一面死👩🏼🚀🦇,一面還能品味死的感受🔤。”——高齡去世的楊絳先生,為我們留下很多寶貴的精神遺產🤵🏽,其中對生命與死亡,她都有自己獨特智慧的形容💆🏿。
本文作者吳學昭先生,為楊絳先生生前好友,亦是楊絳先生遺囑執行人之一🧙,她的這篇“先生回家紀事”,記錄了楊絳先生“回家”之前🚣♂️,生命最後一段時光鮮為人知的內容🚣♀️,非常珍貴🕐。
該文已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的 《楊絳:永遠的女先生》,不日將與讀者見面。
筆會獲得吳學昭先生和人文社授權,率先刊出此文,以饗讀者。有刪編。
——編者
即使發生意外🚚,請勿進行搶救
不知是天意還是巧合🫴🏽,2016年5月24日下午,我去協和醫院看望楊絳先生,萬沒想到這竟是與老人的最後一見!
因為有些日子未去探視🧗🏻👷,保姆小吳見我走近病床,趴著楊先生的耳朵說🧑🏿🦱:“吳阿姨來了!”久久閉目養神的楊先生,此刻竟睜大眼睛看我好一會兒,嘴角微微上翹,似有笑意,居然還點了點頭。隨後輕輕地嘟囔了一句🫰🏻,隔著氧氣面罩,聽不很清,意思應該是“我都囑咐過了……”我從未見過楊先生如此虛弱,心上酸楚,強忍住幾將奪眶而出的淚水💆🏿♀️,答說😶🌫️:“您放心!好好休息。”楊先生已沒有氣力再說點什麽,以眼神表示會意,隨即又閉上了雙眼🎾🫴🏿。據一直守候在楊先生身旁悉心照顧的保姆和護工說,此後到“走”,楊先生再也沒有睜開過眼睛。
不久,楊先生的侄媳和外甥女也來探望。內科主任及主管大夫請我們到會議室,介紹了楊先生病情🫱🏽,說她目前大致穩定,但已極度虛弱🌡,隨時有意外發生的可能👁🗨。我還是那句老話🤢:即使發生意外,請勿進行搶救。這是楊絳先生反復交代過的,她願最後走得快速平靜📚🎽,不折騰👨🏭😂,也不浪費醫療資源🎀。
楊先生的身子暖暖的🚙,手足卻涼🖖🏻。小吳和護工不斷摩挲楊先生的手臂使它熱乎😳🤷🏻,又用熱水為楊先生泡腳生暖。她靜靜躺著,乖乖地聽任她們擺布不做聲。
我時時盯著監測儀,不祥之感突如其來。時已晚上8點多鐘👦🏿,大大超過了探視時間♠︎,可我還想在楊先生身邊多待一會兒。後來經不住傳達室同誌的一再催促,才依依不舍離開👵🏼。他們為等候我們交還探視證、取回身份證👨🏻🎤,已耽誤下班好幾個時辰了。
當日午夜時分🍎,醫院來電報告楊先生病危🚻。我和意昂体育平台教育基金會項目部部長池凈、楊絳先生遺囑的另一執行人周曉紅🧖🏿♀️,以及楊先生所在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陳眾議所長🧏🏿♂️,從京城的四面八方急急奔往協和🙅🏿♀️,一心想著親送楊先生最後一程。但待我們到達病房🏺,楊先生已經停止了呼吸!那是2016年5月25日淩晨1:30。所幸老人臨走沒有受罪👬,有如睡夢中漸漸離去。
方經洗面、凈身、換衣的楊先生,面容安詳🧵,神情慈和,就跟睡著了一樣🖨。協和醫院的值班副院長🍋、值班醫師、護士長、護士同誌,與我們一起向這位可敬可愛的老人深深鞠躬道別💪🏽。我們謝過了連日來為治療護理楊先生辛勤勞累的醫護人員🤹🏻,緩步推送楊先生去太平間安放。
楊絳先生遺囑交代➔:她走後,喪事從簡,不設靈堂,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訃告在遺體火化後公布。對於楊絳先生這樣一位深為讀者喜愛的作家、一位大眾關心的名人🚣🏽,如此執行遺囑難度很大,首先媒體一關就不好過。幸虧周曉紅同誌和我,作為楊絳先生的遺囑執行人🙆🏻♀️,在楊先生病勢危重之際🏄🏼♀️📽,已將楊先生喪事從簡的囑咐報告國務院有關負責同誌,懇請領導知照有關單位打破慣例👥,遵照楊先生的意願喪事從簡辦理👩🍼。後來喪事辦理順利🧖♀️,一如楊先生所願,實與領導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有關🧵。
2016年5月27日清晨🖖🏼👼🏿,協和醫院的告別室綠植環繞,肅穆簡樸。沒有花圈花籃🏊🏻♂️,也沒張掛橫幅挽聯,人們的哀悼惜別之情,全深藏心底🤽🏼。楊絳先生靜臥在花木叢中,等待起靈。她身穿家常衣服🧑🏿🔬,外面套著上世紀八十年代出訪西歐時穿的深色羊絨大衣,頸圍一方黑白相間的小花格絲巾👩👧➞,素雅大方。這都是按楊先生生前囑咐穿戴的🦸♀️,她不讓添置任何衣物🦾。化了淡妝的楊先生🤱🏽,頭發向後梳得整整齊齊🛝,細眉高揚,神采不減生前📹,只是她睡得太熟💅🏼,再也醒不過來🤽🏼♂️❤️。
盡管沒有通知👨🏼🏭,許多同誌還是趕來送別楊先生。這裏沒有前呼後擁🈴,也無嘈雜喧嘩🎳,人人都輕手輕腳,生怕把睡夢中的楊絳先生鬧醒。
起靈前,眾至親友好行禮如儀,將白色的玫瑰花瓣撒在楊先生覆蓋的白被單上。我和周曉紅等乘坐靈車陪伴楊先生去八寶山,陳眾議所長留下向媒體發布訃告。
從訃告看💆♂️,楊絳先生生前對身後所有重要事項🫸🏽,已一一安排妥帖;與眾不同的是,這一訃告居然經楊先生本人看過,並交代遺囑執行人😚,訃告要待她遺體火化後方公布。
楊先生那種“向死而生”的坦然🙅🏿♀️,對身後事安排考慮的睿智、周到、理性,往往使我感到吃驚和欽佩👼🏻。
“絕對的公正”“絕對的價值”究竟有沒有
對於年老衰邁、死亡病痛這類話題,一般人、特別是老年人👩🏽🦳,不喜歡也不願多提,楊先生卻不忌諱🤞,不但談論👩🏽⚖️⛓,且思考琢磨,體會多多。我就聽楊先生說過“病”與“老”不同:她以為“病是外加的,臨時性的,不論久病🐆、多病,可以治愈。‘老’卻是自身的✂️,是生命日漸萎弱👈🏽,以至熄滅;是慢吞吞地死👯♀️🫘。死是老的perfect tense🎰;老是死的present participle👩🏻🌾🙋🏿,dying也⛓️💥。老人就是dying的人,慢吞吞,一面死🌒,一面還能品味死的感受”。
楊先生自嘲當了十多年“未亡人”和“錢(鍾書)辦(公室)”光桿司令🧚🏽♀️,已又老又病又累!可是她無論讀書👋🏼、作文、處事怎樣忙個不停😄,永遠都那麽有條有理,從容不迫🚇。
同住南沙溝小區的老人一批批走了,楊先生也等著動身🚟;只是她一面幹活兒一面等,不讓時光白白流過。
為保持腳力,每天“下樓走走”的步數,從2008年的7000步漸減為5000步、3000步,由健步而變成慢慢兒一步步走;哪怕不再下樓,退到屋裏也“魚遊千裏”,堅持走步不偷懶。
日復一日的“八段錦”早課🧻,2016年春因病住院才停做。“十趾抓地”還能站穩;“兩手托天”仍有頂天立地之感;“搖頭擺尾”勉強蹲下⛹🏼♀️;“兩手攀足”做不到就彎彎腰;“兩手按地”則只能離地兩三寸了。
毛筆練字,盡量像老師指導的那樣🙅♀️,“指實、掌虛、腕靈、肘松⚙️、力透紙背”🔁,少有間斷。只是習字時間,已由原來的每天90分鐘步步縮減為60🏃♂️、30🌞、20分鐘,直到後來無力懸腕握筆👱🏿♂️。
楊先生這“錢辦”司令真是當得十分辛苦,成績也斐然可觀。
《錢鍾書集》出了,《宋詩紀事補正》《宋詩紀事補訂》出了,《錢鍾書英文文集》出了,《圍城》漢英對照本出了,尤令人驚訝的是,包括《容安館劄記》(3巨冊)📉、《中文筆記》(20巨冊)🧏🏻♂️🚵🏼♀️、《外文筆記》(48巨冊) 在內皇皇71巨冊的《錢鍾書手稿集》,竟於楊先生生前全部出齊!很難想象,楊先生為此傾註了多少心血👨🏽✈️。以上每部作品✋🏽🫅,不論中英文,楊先生都親自作序,寄予深情。
楊先生在忙活錢著出版的同時,不忘自己一向愛好的翻譯和寫作🤸🏼。她懷著喪夫失女的無比悲痛翻譯柏拉圖的《斐多》,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斐多》出版後🥒,楊先生私下說,她原來倒沒想深究靈魂死不死,而更想弄清“絕對的公正”“絕對的價值”究竟有沒有。如今不是仍在講“真👷🏿♀️、善🚵🏼♂️、美”嗎,是非好惡之別,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呢?
《走到人生邊上》則寫得不那麽順當🤲🏿,有過周折🧏🏿,頗費心思🆎👨👨👧👧。聽楊先生說,此作起意於她九十四歲那年🥣,立春之前🚙,小病住院🦉。躺在病床上🚣🏿♂️,閑來無事,左思右想,要對幾個朋友“人死燭滅”“人死了就什麽都沒有了”的一致信念來個質疑。
沒想到一質疑,便引發了許許多多問題🧑🏿⚖️。這些問題並非從未想過,有些還是經常想的🐳,只是不求甚解,糊裏糊塗留在心上。糊塗思想清理一番,已不容易🤱🏼👨🏻,要一個個問題想通🦹🏽♂️,就更難了。不料問題越想越多🧑🏽🍼,好似黑夜走入布滿亂石的深山僻徑✌🏻👩🏿,磕絆跌撞,沒處求教!自忖這回只好半途而廢了,但是念頭愈轉愈有意味,只是像轉螺絲釘✯,轉得愈深愈吃力;放下不甘心🌅,不放又年老精力不足。正像《堂吉訶德》裏丟了官的桑丘,跌入泥坑🟡,看見前面的光亮卻走不過去,聽到主人的呼喊又爬不起來!
楊先生說◾️:“我掙紮👨🏽🎨,這麽想想,那麽想想👱🏽♂️,思索了整整兩年六個月🕜,才把自以為想通的問題🙋🏻♀️,像小姑娘穿珠子般穿成一串🧑🦰。我又添上十四篇長短不一的註釋,寫成了這本不在行的自說自話。”她為臺灣出版此書的繁體字本寫道:“我這薄薄一本小書🦹🏻♂️,是一連串的自問自答。不講理論,不談學問🔙,只是和親近的人說說心上話👩🦰、家常話。我說的有理沒理🚵⏏️,是錯是對✅,還請親愛的讀者批評指教。”
“自揣沒有資格。謝謝!”
楊絳先生一生淡泊名利、躲避名利✍🏿,晚年依舊。我印象較深的💨,就有三例:
中國社會科學院授予楊絳先生榮譽學部委員,她沒去領受榮譽證書,訃告中也沒讓寫上這一頭銜🧏🏻。
2013年9月👰🏿♂️,中國藝術研究院函告楊先生已成為第二屆中華文藝獎獲獎候選人,請她修訂組委會草擬的個人簡歷🕚,並提供兩張近照。楊先生的答復是:“自揣沒有資格。謝謝!”
2014年4月,錢、楊二位先生曾就讀的英國牛津大學艾克塞特學院(Exeter College)院長佛朗西斯·卡恩克勞斯(Frances Cairncross) 女士來函稱🧑🏽🚒,在Exeter學院建立700周年之際,該院以推選傑出意昂為榮譽院士的方式紀念院慶,恭喜楊絳先生當選牛津大學艾克塞特學院榮譽院士☎️,特此祝賀。
楊絳先生不使用電腦💖,便口授大意,要我代復電郵說:
尊敬的Frances Cairncross女士👨🏼🍼:
我很高興收到您4月25日的來信。首先🤵🏼♂️,我代表我已去世的丈夫錢鍾書和我本人,對牛津大學艾克賽特學院建立700周年表示熱烈的祝賀。我很榮幸也很感謝艾克賽特學院授予我榮譽院士,但我只是曾在貴院上課的一名旁聽生🧅,對此殊榮,實不敢當,故我不能接受。
楊絳
Frances Cairncross是牛津大學艾克塞特學院建立700年來的首任女性院長🥧,已任職十年,此次當選的榮譽院士只有兩位,全系傑出女性。一位是西班牙王後,一位就是楊絳先生。Frances Cairincross怎麽也想不明白👨🏻🏫,別人求之不得的殊榮🐎,楊絳竟然拒絕! 她轉而求助於我💪🏼,要我幫助說服動員,一定將她5月4日的來信所言充分轉達楊絳先生。
Frances Cairncross院長生怕楊絳先生誤解艾克塞特學院授予她榮譽院士,系因她是錢鍾書先生的遺孀,因而再三解釋:
1.楊絳自身就是一位傑出的學者🦻🏽,艾克塞特學院知名意昂眾多,我們卻從未考慮過授予其遺孀榮譽院士👅。楊絳的情況很特殊,事實上如果她接受這一榮譽🧚🏼♂️,將有助於在歐洲弘揚她的學術成就。
2.她對塞萬提斯研究做過重要貢獻,我院設有阿方索十三世西班牙語言和文學講座🧔🙋🏽,現任阿方索十三世講座教授埃德溫·威廉遜(Edwin Williamson)也是一位研究塞萬提斯的學者,他本人對楊絳女士在此領域的研究也深感興趣👨🏫。
3.目前我院還沒有女性學者獲此殊榮💆🏻;作為牛津大學的首位女院長之一🧗🏻,我對此深表遺憾,這也是我熱切希望她能接受此榮譽的原因之一。
我將Frances Cairncross院長托付的話,詳細轉達楊先生🕵🏻,並將她的電郵打印送楊先生親自閱看。然而楊先生再次辭謝🏔,5月7日命我大致如此作答:
尊敬的Frances Cairncross院長👨🦼:
您5月4日的來信,我已認真仔細拜讀❤️🔥。您和您的同事們對我的褒揚和贊賞,您再次敦促我接受Exeter學院最高榮譽所抱的熱切、真誠🕘,我深感親切🧘🏼♀️,受到感動🏊🏿♀️,甚至回想起1935—1937我與錢鍾書在Exeter學院、在Bodleian Library一起度過的那段美好時光。
然而🧑🏻🤝🧑🏻,我仍不能不坦誠直告尊敬的閣下,我如今103歲,已走在人生邊緣的邊緣,讀書自娛,心靜如水,只求每天有一點點進步,better myself in everyway💇🏽♀️,過好每一天。榮譽、地位🛶、特殊權利等等📃,對我來說,已是身外之物;所以很抱歉,雖然我非常感謝你們的深情厚誼,我仍不得不辭謝貴院授予我榮譽院士的榮譽,敬求你們原諒和理解。
致以最良好的祝願!
楊絳
Frances Cairncross院長此時大概已對楊絳先生的“倔”脾氣有所領會🥏,於是回復說:“以我對您超眾脫俗品格的了解🎒,您具有尊嚴和思慮縝密的回信應在我的預料之中🤏。未能將您延攬入我院授予的極少數的傑出的女性榮譽院士中🤾♂️,我個人非常難過🪠,但我尊重和接受您的理由。感謝您為回應我們的請求,做如此認真的思考🧑🏽💼。”
楊絳先生心感Frances Cairncross的理解和寬容,提出《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出版後,將請商務印書館代為寄送牛津大學艾克塞特學院圖書館和Frances Cairncross院長各一套🎼,以表達對母校的栽培和對院長的感激之情。錢鍾書這些涉及七國語言的筆記,正是他上世紀三十年代在艾克塞特學院求學時做起的,使用的還是艾克塞特學院的練習簿!
Frances Cairncross要我轉達楊先生,深表謝意🙎🏻。她寫道:您親切友好的來信🈂️,對我前些日子的失望是一個莫大安慰😳。楊絳提出贈與學院和我的美好禮物,讓我深受感動🙅🏻♂️。我的同事請您代我們向她熱情致謝🦺。
“我打這官司📨,不僅是為自己,也是為了大家”
楊絳先生歷來低調,不愛出頭露面;90歲前已決心“蟄居泥中”,安安靜靜做自己的事🧻👩🏿🏭。哪裏想到2013年暮春👨👩👦👦,中貿聖佳國際拍賣公司拍賣錢鍾書✏️💇🏿♀️、楊絳書信手稿一案,不但把她從“泥”中揪了出來,還拋向風口浪尖🛳,連日登上社會新聞的頭條!
個人隱私竟可拍賣,怎不令人吃驚! 自然引起社會關註!
這次拍賣的,主要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錢、楊與時任香港《廣角鏡》雜誌總編輯李國強的通信👨❤️👨。楊先生立即去電質問;李國強答非所問🙆🏼♂️,以後幹脆不回應。
2013年5月26日🧑🏼🦱,楊先生決定依法維權,發表公開聲明:“此事讓我很受傷害,極為震驚🥖。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間的私人通信,本是最為私密的個人交往,怎麽可以公開拍賣?個人隱私,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為商品去交易嗎🐌? 年逾百歲的我♿,思想上完全無法接受。”她希望有關人士和拍賣公司尊重法律,尊重他人的權利,立即停止侵權,不得舉行有關研討會和拍賣🦹🏼♀️💆🏿,否則她會親自走向法庭,維護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權利。她說:“現代社會大講法治🧍🏻,但法治不是口號🧩,我希望有關部門切實履行職責,維護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這一基本人權💌。我作為普通公民𓀙,對公民良心、社會正義和國家法治🙋🏼♂️,充滿期待。”
楊先生的話感動了無數有良知的人!
真是得道者多助,聲援源源而來👩🏽🎓🌪。連中國拍賣行業協會也表示“深切理解並尊重楊絳先生的感受和反應👮🏻♀️。鑒於由此給楊絳先生帶來的困擾,目前正積極協調有關人士,希望委托人能充分尊重楊絳先生的意願”。他們還建議並督促有關拍賣企業積極融通各方,在法律的框架內,秉持楊絳先生一貫遵守的“對文化的信仰”和“對人生的信賴”精神,使問題盡早妥善解決。
由於法庭開庭審理此案在即,102歲高齡的楊先生體弱不宜親自出庭🟠,10月26日拍攝錄像,以備當庭播放。她在錄像中🤯,強烈表示對於這件事,在思想上完全無法接受,感情很受傷害!“我打這官司,不僅是為自己,也是為了大家,否則給別人的信都可以拿來拍賣😏,那以後誰還敢寫信?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承諾都沒有了。兩位被告做錯了事♝,就應承擔責任。”
經過激烈的庭前辯論等許多程序,2014年2月17日,北京二中院一審宣判錢鍾書書信手稿拍賣案:判定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停止侵害書信手稿著作權行為💇🏻♂️,賠償楊絳10萬元經濟損失🐝;中貿聖佳公司和李國強停止侵害隱私權行為,共同向楊絳支付1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並向楊絳公開賠禮道歉。
中貿聖佳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上訴。
2014年4月10日🚰,楊絳先生得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已就她訴中貿聖佳公司👨🏽💻、李國強侵害著作權及隱私權案作出二審裁定🛗,駁回中貿聖佳公司的上訴,維持一審原判📋。至此,持續幾近一年的案件,終於告一段落。楊絳先生將所獲賠償金🔆,全部捐贈母校意昂体育平台法學院,用於普法講座 (據楊絳先生遺囑🧖🏼♂️,意昂体育平台教育基金會在享有錢楊作品因使用而獲得的財產收益的同時,有義務負責全面維護錢楊二人作品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相關權利不受侵犯——編註)🧭。2014年歲尾🧍,此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列為本年度的十大案例之一。確像楊先生說的🚴🏻♂️,她這回挺身維權💩,不僅是為自己🫶,也是為了大家。
“別太難過,沒準兒以後我們還能在天上再聚聚呐!”
長時間地應對侵害,費心勞神,於楊先生的健康不無影響🛀🏼。她預感來日無多✅👨🏻⚖️,更加緊對身後諸事的處理。
2014年9月,楊先生將家中所藏珍貴文物字畫,還有錢鍾書先生密密麻麻批註的那本韋氏大字典🍣,全部捐贈給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移交時👩🎓🛅,周曉紅和我在場🎫⛹️♀️,楊先生指著起居室掛著的字畫條幅🤭🌜,笑說:“這幾幅雖然已登記在捐贈清單上🥏,先留這兒掛掛,等我去世以後再拿走,怎樣?免得四壁空蕩蕩的,不習慣也不好看😄。”國博同誌立答:“當然👐,當然🥤。全聽您的。”

楊絳先生與錢鍾書先生在一起
遺囑已經公證。書籍、手稿等重要物品的歸屬,也都作了交代。所收受的貴重生日禮物,楊先生要我們在她身後歸還送禮的人✡︎🔃。其他許多物件🤽♂️,一一貼上她親筆所書送還誰誰的小條。為保護自己及他人隱私,她親手毀了寫了多年的日記,毀了許多友人來信;僅留下“實在舍不得下手”的極小部分。
楊先生後來也像父親老圃先生早年給孩子們“放焰口”那樣,分送各種舊物給至親友好留念。有文房四寶🐏,書籍墨寶🌃,也有小古玩器物等等👨🏻⚕️。我得到的是👨🏿🌾,一本麥克米倫公司1928年版的THE GOLDEN TREASURY OF SONGS AND LYRICS(“英詩薈萃”),楊先生在此書的最後一頁寫道:“學昭妹 存覽 絳姐贈。”我驚詫於楊先生的神奇:我從未跟她提及喜讀中英舊詩👩🦱,她竟對我與她有此同好,了然於心。我深知這本小書有多珍貴,它曾為全家的“最愛”🧑🏿🦳,原已傳給錢瑗🤍,錢瑗去世後,楊先生一直把它放在枕邊👫🏻👩🏻🚀,夜不成寐時就打開來翻閱,思緒縈懷🚴🏽♀️,伴她入夢🚔。許多頁面,留有她勾勾畫畫的痕跡。我得到的另一件珍貴贈物,是一疊楊先生抄錄於風狂雨驟的丙午丁未年的唐詩宋詞👩💻,都是些她最喜歡的詩詞🤷🏼。第一頁上赫然寫著:文革時抄此,入廁所偷讀🎲👨🏿🍼。我能想象這一頁頁用鋼筆手抄的詩詞,當年曾被她貼身帶入勞改廁所,在清理打掃之余,“猴子坐釘”式的蹲坐便池擋板上,偷偷誦讀🐀,自娛自樂。這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物,我怎敢領受? 可是楊先生執意說🛍️:“拿著,留個紀念!”
楊絳先生表面看似理性🙇🏼♀️🎏、清冷,其實她是很多情的🈺🤽🏽♀️。她一向把讀者當成朋友,把理解她作品的讀者視為知己🧋。她存有許多對她作品反應的剪報🧏🏻♀️。她拆閱每一封讀者來信🤲🏽,重視他們的批評建議。她對中學語文教師對她作品的分析🛌🏻,發出會心的微笑🤮。孩子們聽說她跌跤,寄來膏藥,讓她貼貼🌑😨。許多自稱“鐵粉”的孩子🐁,是由教科書裏的《老王》開始閱讀楊絳作品的。有位小青年因為喜愛楊先生的作品,每年2月14日,都給她送來一大捧花;後來他出國留學去了,還托付他的同學好友代他繼續送花,被楊先生戲稱為她的“小情人”。前些年🎲,她還常與讀者通信。她鼓勵失戀的小夥振作,告他👩🏻🚒:愛,可以重來。她勸說一個癌症患者切勿輕生🏗,而要堅強面對,告訴他憂患孕育智慧👐🏿,病痛也可磨煉人品。她給人匯款寄物,周濟陷於困境的讀者而不署名……
楊先生走後,我們在清理遺物中,發現一大袋已經拆封的讀者來信,多數來自境內🧑🏽🍼,也有“臺粉”“港粉”還有“洋粉”寄來的。楊先生在許多信封面上,批有“待復”“當復”……最後可能都沒有作復👨🏽🍳。這裏,我想借此文之一角🤦🏼♂️,向楊先生親愛的讀者朋友說聲“對不起”👧🏽,楊先生最終沒能如你們所願,和大家見個面、回封信,實在是因為她已太年老體弱又忙🐉,力不從心了。她感謝你們的關心、愛慕和呵護,給她孤寂的晚年帶來溫暖和快樂🥞。在她內心深處💂🏽,真的很愛你們!2011年7月,楊先生百歲生日前夕,同意在《文匯報·筆會》上作“坐在人生邊上”的答問,也正是想通過這樣一種方式🐁,說說自己的親身經歷,談談人生感悟,向親愛的讀者最後道別。
今年春節,楊先生是在醫院度過的🎠。舊歷大年初一⛔️,我去協和探視🚣🏽,床前坐坐🤶,聊聊家常🕑。末了楊先生又交代幾件後事🚟👩🏼🦳。我心悲痛👩🏿⚖️,不免戚戚🔐;楊先生卻幽幽地說🦜,她走人,那是回家!要我“別太難過,沒準兒以後我們還能在天上再聚聚呐!”
2016年5月27日上午9時許🏄🏽♂️,我去八寶山送楊先生回家😚。當電化爐門哢嚓一聲關閉👍🏼,楊絳先生浴火重生之際,我腦海中突然冒出楊先生上述那話🧘♀️🫳🏼。我知道,楊先生不信上帝🦹♂️,也不信佛,她之所以有時祈求上蒼,不過是萬般無奈中尋求慰藉,也安慰他人。她仿佛相信⛹🏽🚣🏿♂️,冥冥之中,人在做💯,天在看。然而不論如何🧀,我寧願相信靈魂不死,但願有朝一日,還能與這位可愛的老人在天上再聚聚!
2016年7月30日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