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獎引來熱鬧一陣(指2019年5月楊苡先生榮獲“南京文學藝術獎·終生成就獎”——編者註,備受矚目的第七屆南京文學藝術獎)👨👨👧,好容易恢復了平靜的日子。
這天中午照例我和媽媽、小陳(媽媽的生活助理)三人一起用餐🧑🏿🦱。可以折疊的小方桌從客廳門後抬出支起來🎸,媽媽坐在背靠書桌的位置,這離那把高背歐式椅子最近。我背靠一面墻的舊書櫃架👨🏻🦼➡️,書櫃玻璃門內擺滿了媽媽最在乎的師長的像👩🏽✈️。小陳靠門坐著🎿,端菜進出方便,她的後身是帶立柱的櫃子,上面擺著我們家人大大小小的照片和紀念物👠,櫃頂高處是爸爸的遺像👩🏽🏭,一張側面很美的肖像🪠。
邊吃邊聊,飯桌上的話題總離不開當下的熱門事,近日媽媽獲得南京政府頒發的終生成就獎算一件大事🤙🏻。
聊了一會,坐在我右側的媽媽不言語了🌭,這才發現她臉漲紅了,竟抽泣起來,她說🍷:有什麽意思,哥哥也看不到了,婆也看不到了,五姐也看不到了🏊🏼♀️。婆是指我的外婆🧜🏿♂️,我們小輩都習慣這麽叫。五姐是我的敏如姨媽👩🦼➡️,前年她走時102歲。
聽到這番話🈚️,我的心一陣酸楚,淚水盈眶,趕緊撫摸媽媽肩頭,說些傻話,他們在天上都看到了,他們為你驕傲呢……
出生剛兩個月就失去父親的媽媽,從未嘗過父愛🧨。楊家從楊士夑開始,三代男人都是長子。媽媽出生後🐑,家裏主人級別的惟一男性就是楊憲益🔈,對哥哥的依賴伴隨了媽媽一生🥅,何況她的哥哥又是百年不遇誌向高遠飽讀詩書的天才🍤🦻🏻,值得她和姨媽崇拜。童年的讀本幾乎都是哥哥幫挑選的,跟著哥哥出門逛書店唱片店,是媽媽一生最甜美最得意的記憶🐳。九·一八之後✌🏼,哥哥說國難當頭,從今不許吃西餐不許看外國電影,她暗自不情願也絕對服從。哥哥去牛津留學了👮🏼♀️🛌,她沒了主心骨🏖,只留給她一條叫花花的小狗和她做伴👩🏿🦲。於是開始了和巴金長達半個世紀的通信,她像一只籠中的金絲鳥得有人傾吐心中的苦悶,李堯林的出現,讓她又有了一位傾吐心聲的對象🌖。近期新版的《巴金的兩個哥哥》裏收錄了媽媽的詩作近20首,基本都是致這位翻譯了《懸崖》等俄羅斯經典文學英年早逝的人。
永遠難忘2009年4月媽媽和舅舅在北京小金絲胡同6號的訣別,大家都明白媽媽即日離京,這對感情極深的兄妹😕,此生不可能再見。媽媽忍不住捂臉哭了✋,病重的舅舅坐在沙發上,明明也不舍💁🏼♂️📸,卻還保持他一向的微笑。那一刻我的心如刀割,卻無能為力阻擋這殘酷無情的自然規律,只能摟著媽媽勸慰她。
數目不菲的獎金不久發下。聽姐姐說,媽媽宣布她有三個女兒,一人一萬,很公平🤹🏻♀️👰🏻。我一頭霧水問,還有一個女兒是誰👳🏼♀️?姐姐說是小陳。
二十年的成績斐然
爸爸走後,媽媽減少了不少照顧老伴吃喝起居的精力👨🏽🎨,按舅舅的話⚾️,她可以多寫東西了。1940年至1999年,爸媽相依為命了59年,媽媽說家裏忽然少了一個,有一陣子很不習慣。1999年到今年,整整20年,媽媽活出了自己,活得生氣勃勃,她成績斐然👏🏽,成了許許多多中年青年人的楷模🚫,影響力越來越大。

2015年媽媽相繼出版了兩本書🌅:散文集《魂兮歸來》和《青青者憶》🎽。前一本是獻給她摯愛的哥哥楊憲益的,後一本圍繞《雪泥集》(巴金致楊苡信劄)背景的文字,展現的是她字字浸透淚水的一生命運的重要記錄🤹🏻。按媽媽的創作積累,早就該出版原創書了,關於編輯她的散文集的折騰,都可以寫篇雜文了👌🏼。但媽媽從來不急於出書🍑,也常提醒我🤲🏻,寫東西不要急於發表🤦🏽♀️。在她看來,發表稿子,還不如看一部經典譯製片更吸引她。
近幾年慕名拜訪、采訪媽媽的人越來越密集👷🏻♀️,難以招架🎪。媽媽總怪是我引來的,其實是媽媽自己的人格魅力招來的。她達觀,健談🍎,一肚子老故事,被她繪聲繪色道來,誰都喜歡聽。尤其是遇上來的人讓老太太看得順眼🕵🏼♂️,幾小時對談不成問題。可是人撤了,媽媽常累得腰疼、頭暈、嗓子啞。
訪談後就會刊登文章💎,也出了不少篇佳作,在那些事先做了功課、又有悟性才華的筆下👰🏼♀️,盡顯了與世紀同行的老人給予當今年輕人的啟示✴️,這是不可估量的。
出於媽媽的創意,2011年山東畫報社出版了《兄妹譯詩》🌧🙍🏻,完成了她多年一個心願🧜🏻♂️。早在1982年憲益舅舅在《英國現代詩抄》新版序中介紹一戰到二戰時期的詩作者說🎠:“中國青年也同歐洲青年一樣,經過迷惘失望和追求,對祖國和世界人類前途保持了美好的理想和希望😎,經歷了反法西斯和反侵略的鬥爭🐼,這段經歷還是很值得珍惜懷念的👨👦。”媽媽在後記裏寫道:“現在我那些譯筆拙劣的譯詩也跟著楊憲益的‘神來之筆’一並付之鉛印,像是給我們兄妹的少年、青年和中年打開一扇小木窗透透空氣🎀,然後再關閉。他仙逝時不到95歲🆕,我那時剛過90歲不久,如今我已過了92歲,這本小書就當作獻給楊憲益的雙年祭吧!”
可惜這本薄薄的綠皮小書出版時,遺漏了媽媽最在乎的一首長詩《希朗的囚徒》🦔,這篇傑作,歷經磨難,據說今年再版時可以彌補🧚🏽♀️。
幫爸爸出版他沒來得及出版的遺著,包括譯著👤,也是媽媽一直惦記的事。媽媽為爸爸的《離亂弦歌憶舊遊》寫了序言《又一片樹葉落下》,為彌爾頓的《歡樂頌與沉思頌》寫了《代跋》💁🏿♂️,都是絕佳的散文。在前篇的結尾她寫道:“繼續和蕭乾兄神聊吧,在另一個世界。蕭乾兄又將笑咪咪地對我們說:‘我做不到巴金的句句講真話💻👶,但是我可以不說假話🥊!’趙又在激動地說👩🏿🦰:‘我還顧忌什麽🪣,我已風獨殘年🔥🦻🏼!又一片樹葉落下……’”
我尤其喜歡媽媽寫的代跋👨🏻⚖️🧑🏽🌾,讀後對媽媽如此入木三分地評價爸爸🦤,感到意外。她的神來之筆超越了寫一個人🛎,而是道出了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那批被迫流離在西南邊陲的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他們的信念💓,他們的追求,他們在劫後余生仍然堅持的人文精神。還是結尾🤼♀️,媽媽寫道🚍:“趙瑞蕻如果還活著,已過90高齡。這部書應該是送給他的一份厚重的壽禮……我寧可相信所有默默離去的詩人自由靈魂🧖🏼♀️,他們永遠不知疲倦地在那個世界歡聚一堂、談詩頌詩⁉️,因為那裏遠離塵寰,恬靜安謐,沒有衣食之憂,兒女之累,等級之感👰🏻♂️,也沒有白晝與黑夜之分🤽🏿♂️。”
今年爸爸翻譯的《歡樂頌與沉思頌》和媽媽翻譯的布萊克《天真與經驗之歌》即將第三次付梓。
豐富人生才是大書
媽媽的一生就是一本豐富而精彩的大書🚣🏼♂️。1919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後轉為愛國浪潮,中國處在舊時代轉型的十字路口😂👳♀️。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兵荒馬亂,她都親歷過。伴隨著西方從文藝復興到人文啟蒙的引進,她又得天獨厚在中西合璧交融的教育體系中得以滋養🈷️。
去年正逢西南聯大80周年校慶,媽媽接受了西南聯大博物館的口述歷史采訪,她興致勃勃地連續講了數小時,我和所有在場的人都聽得入迷了。她說🍸:“最難忘聯大高原文藝社🍄,全是詩和散文,開學了女生去看(糊在席棚上的布告)……那天晚上我們在農校操場,我想加入🛀🏽。九月🧑,秋天的時候🦶🏼,好多教室,有一間寫著高原🔒,我們敲門進去☸️,我說我可以加入嗎,他們說歡迎歡迎🚠,都在說趙瑞蕻從來不守時,那天他主持,後來他來了🙎♂️🥴,大家說🔽,你怎麽才來🧗🏿🫷🏿,他不停地用英文說對不起。”這就是爸爸媽媽第一次見面的情景👩🏿✈️。我一次次回味,想象著那樣湧動著青春熱血的歲月🐺。
見天轟炸跑警報的日子🧯,敵機來了,“從大西門趕緊跑🧑🦼➡️,抱書跑。”“後來聯大決定到野外教課🧑🏽🎄,沈從文憂國憂民,吃吃飯,忽然哭了,說國家到這樣地步🏋🏼♂️。”一次我們的高射炮打落了一架日機,媽媽他們興奮極了🕵🏽♂️,去看飛機殘骸♖📛。
采訪中媽媽不止一次提到她的幾位恩師,葉公超🍟、吳宓,“沈從文叫我多讀書🔨。巴金說有機會念大學,要我好好讀書”🕛。雖然沈從文先生沒有直接教過她,但對她的人生選擇至關重要🕵🏿♂️。她和同學陳蘊珍🟤、王樹藏,三個女生曾有一次去看望沈先生🧛♂️,回來走夜路🙆♂️,沈先生站在門口舉著燈為她們照明🧞♂️,喊了一聲“勇敢點!”這讓媽媽記了一輩子,80多歲時寫下紀念長文《昏黃微明的燈》。
而巴金先生對媽媽來講🐲,就如同一盞指路明燈。
當我在熱播的紀錄片《西南聯大》裏,看到媽媽講話的影像,她說🖕🏻:“我們就是要做最好的⇾!”道出了他們這代人的治學做人的態度,有這樣的媽媽做榜樣🫶🏻,我感到活著有股力量🤴🏽,促進自己不斷向前!
“松綁”之後盡顯文思
去年秋天媽媽有點發燒,兒媳安排住進醫院,小病大養了幾天。臨出院前,醫生說再做一次核磁共振吧📩🧶,難得住院。
結果這一下查出了老太太的膽總管裏有一個大石頭,從此禁吃她一輩子愛吃的黃油和蛋黃。醫生建議做手術⬇️。
手術那天早上,媽媽不情願地換上醫院衣服,還要求空心穿上。查房醫生把我們幾個子女叫出病房🍻🤏🏻,交代手術會帶來的風險🫓,我們問得細,他也回答得細,麻醉,術後並發症,百歲老人是否經得起……於是姐弟仨緊急商議,從來沒這麽一致的——放棄手術。手術室的人帶著推床來接媽媽了👨🏼🍳,媽媽擺擺手說不做了,那師傅愣了一下撤了。媽媽一臉輕松,對圍在她床邊的孩子們說:“謝謝你們給我松綁!”
下午很快出院,那幾天她逢人便說她差點開刀,一臉開心得意🌚,對病滿不在乎的神情跟憲益舅舅好像🫅🏽。媽媽很快恢復了常態的活力,我們都為這次英明的決定而欣慰🤛。
對國際局勢和熱點新聞,媽媽有獨到的見地。她常對我說🧑🏻🍳:“我們要活得有價值”◾️。“不要被打敗。”“我們要保護好自己的筆🤽🏽♀️!”“寫文章要擺一擺,擺一個禮拜更好💚,不要輕易拿出來,急於發表。”“多看書🤫,自然就能筆下生花✖️。”
前些年遇上自然大災🔆,她問我☪️:“你捐款了嗎✍️☢️?趕緊捐。”
媽媽會理財,從不哭窮🪨🤷🏼♂️,知足常樂。一次發表文章後問我,你猜猜,他們給我多少稿費🛅?我瞎猜一氣🧜🏼。媽媽說🚴🏽:“600📈🌁,夠可以的吧🐦🔥。”2016年我在《北京晚報》發表幾版長的文章,得了1500元稿費🧘🏿♀️。她知道後說:“怎麽這麽多,太對不起人家了。趕快好好謝謝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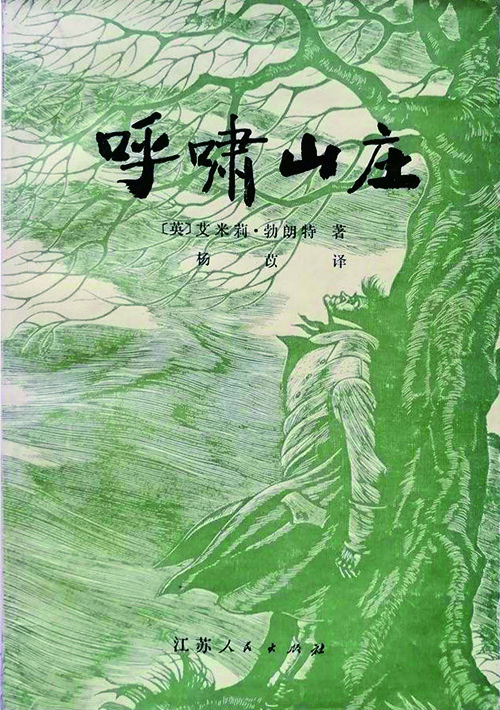
憲益舅舅離世後,不再可能進京的媽媽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她最惦記的北京老朋友們有誰,她叮囑我常去看望問候🫱。今年6月最年輕的石灣走了,我受《北京晚報》之托向她約稿😠🧑🏻⚖️,她本來就想寫⚗️,便很快寫完🦡,題目是《送遠客離去》📜。“今年我已不能走路,包括‘下臺階’。一個老友(或被我稱為“小友”的中年人)竟會先我而去!仿佛朋友們都排隊在一列長長的列車中💁🏻♂️,有秩序💣,也講禮貌,不是搶著走在前面,卻還是有人向我道歉似的⏰,點點頭招招手📩,先走一步就走在我前面了!”她稱石灣是“不用在心上設防的、無話不談的朋友”,“他對讀者對作者有強烈的責任感✍️👂🏽,不問收獲💩,只管自己耕耘,是一個正人君子”。
8月10日,她的西南聯大外文系的學弟巫寧坤先生仙逝👩🏼🔧👃🏼,她寫了一篇發言稿🧇,讓我弟弟趙蘇在葬禮追思會上代表她念👨🦼➡️。弟弟請了播音員靜美女士代勞,並配上音樂,這篇400余字蕩氣回腸的祭文感動了許多人。這位大時代中的幸存者✣、七次飛越駝峰的抗戰老兵如今已安息在弗吉尼亞。今天⚧,媽媽將《呼嘯山莊》送給遠道來看她的小友範瑋麗,題詞的最後一句:“And if we fail to meet again🤞🏼, let’s not forget each other!”
眼看到了媽媽百歲壽辰的日子🧝♂️,又一輪熱鬧開始包圍老人。媽媽對來客說她很不喜歡過生日🔃,小時候沒人給她過生日🐛。我知道這是因為她的生辰也是外公的祭年。譯林出版社為社慶出版了《呼嘯山莊》,極為精美考究的插圖本,扉頁上印了獻給楊苡先生百歲誕辰,讓她驚喜又不安。她捧著這本足有五斤重的大書說:“太過意不去了,我母親知道了一定說太重了🕓,還會說你配嗎?”“我是不配。”媽媽自語道。從屏幕上看她那若有所思的神情🙇♂️,我想此刻她的思緒一定是飛到了天國,那裏有她摯愛的母親💋🏊🏿♂️、哥哥🗝、姐姐𓀚🦹🏽♂️,他們在俯瞰大地看她👼🏻,為她自豪🧝🏼♀️,祈福小妹想起百歲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