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應镠(1916—1994),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和歷史教育家。1935年夏考取燕京大學歷史系,參加了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自1938年9月至1940年夏在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繼續學習並畢業👨❤️👨。他是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與古籍研究所的創立者,也是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學科的奠基者。在歷史學領域,早期受陳寅恪影響,醉心於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後期因工作需要轉事宋史研究,在這兩方面都留下珍貴的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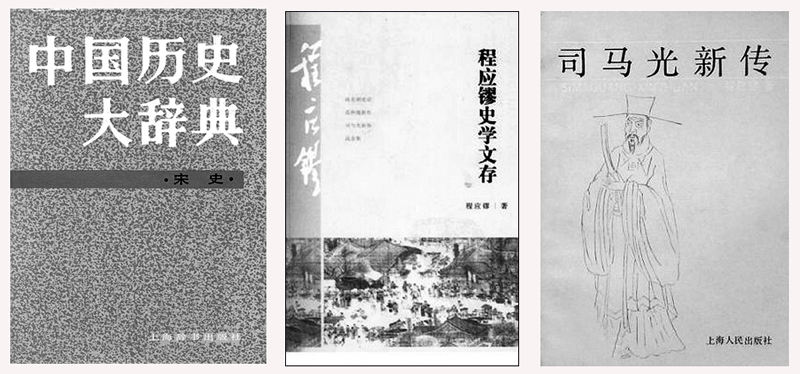

程應镠先生(1916-1994)是20世紀“上海十大史學家”①之。掐指算來,已仙逝20多年🦹🏻♂️。人到老年常念舊。這些年來,我經常想到他⏲,不時講到他🆖🧛🏼♂️。講到他對我國宋史研究的特殊貢獻,講到他的為人與治學之道。想到在他引領下工作的那些日子🤽🏿♀️,想到他留給我的一些不理解或不甚理解的疑問👒。
一
我有幸認識程應镠先生,是因為參加編審《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大辭典》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歷史學界的一項重大工程🦮,由當時資格最老🤕、最具感召力的歷史學家鄭天挺先生擔任總主編,著名歷史學者多半參與其中🎯,擔任分卷主編或編委📌⛷。
據介紹🈹⚔️,這部大辭典“是迄今為止新中國編纂出版的第一部由國家組織編寫的特大型歷史專科辭典”👐,號稱“當今世界上最全面🕹、最權威的中國歷史百科全書”。《大辭典》有14個分卷🥘,《宋史卷》的主編是鄧廣銘𓀏、程應镠兩位先生。因鄧先生忙於編撰《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遼宋西夏金史分冊,《大辭典·宋史卷》由程先生全權負責。
我初次見到程先生,是在上海桂林路100號——現在的上海師大徐匯校區👃🏻。1982年春🧑💻,應程先生之約,我與徐規先生等前輩學者以及朱瑞熙♔、王曾瑜等朋輩先進一同來到這裏🥻,在程先生主持下,編審《大辭典·宋史卷》。
2012年秋,程先生的高足虞雲國教授邀請我到上海師大訪問,我當即欣然應允👨🏽🎨。因為這個“書香惹人醉,花落夢裏回”的地方🫏,給我留下了不少美好的記憶和若幹值得回味的往事🖕。
30年後💂🏼♀️,這裏舊貌換新顏,裝修整飭一新,讓我幾乎無法辨認。經雲國兄提示,我才發現早餐飯廳就是從前的食堂,徐規先生和我等當年在此處拿著飯碗,和同學們一道🚟,依次站立,排隊打飯,然後回宿舍就餐✏️。
下榻的賓館正是當年我們寄宿的招待所👩🏻🦱。當年〽️,外地來的7位學人在此住宿。兩人一間屋,兼做辦公室。剛從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上海師大任教的元史研究生,後來大名鼎鼎的蕭功秦教授和我同住一室。徐規、顏克述兩先生與我們毗鄰而居🛶。
徐規先生是溫州平陽人,每餐必飲老白幹,工作時總要打開收音機聽越劇。越劇聲音開得很大,並不影響徐先生工作。他眼力非凡👆🏽☝🏿,酒後頭腦反而特別清醒🍪,總能迅速發現我們的錯誤,並快速一一予以糾正。
此刻☃️,我仿佛回到30年前的時光🚴🏽,想得最多的⛩、同雲國兄談得最多的無疑是我們的主編程應镠先生。
程先生給我的直覺印象有二🏄🏽:一是體格格外健旺。他身材高大🧘🏿♂️,目光炯炯,有鍛煉身體的好習慣🦠。每天清早都看到他穿著當時很時尚的運動鞋,在學校大操場裏跑步,他年輕時似乎是個體育運動愛好者🦗。二是組織能力超群。他非常講求效益,從不開會閑談,主要依靠曾維華②、虞雲國兩位助手開展工作。行政事務一概由曾維華負責🟢,編審事務則通過其學術助手虞雲國上傳下達。
任務一清二楚,工作井井有條,我們幾乎沒有任何事情和問題需要直接找程先生。
程先生事業心極強👨🏼🏭,為集中精力👵🏽,全力以赴編撰《大辭典》🧑⚖️,他辭去校內一切事務🐢,一人專心致誌在家裏辦公。我們不便打擾,只是晚飯後偶爾到他家短暫拜望。先生頗有長者之風🍎,待人誠懇,樂於助人,有求必應。
當時🐭,我剛調離西藏👶🏽,到四川師大任教,想趁機觀摩上海師大歷史系的課堂教學。程先生立即安排,讓我聽他的大弟子李培棟老師講課。李老師講五代十國,講得十分精彩,至今記憶猶新,給我啟發很大👩🏽🔧。
當年從事國家特大重點科研項目,條件之艱苦,生活之簡樸🕕,在今天難以想象🏌️♂️🫸🏽。參與者無任何好處🫳,每人每天僅有生活補助費3角6分錢。或許是為了彌補一下吧,離開上海前🙆♀️,程先生出資40元✊,請我們在徐家匯衡山飯店吃了一頓淮揚菜,算是“奢侈”了一回。應邀作陪的有早年著有《宋金戰爭史略》一書的沈起煒老先生。其中一道鮮蝦仁炒豌豆,味道異常鮮美,始終讓人回味。
在程先生的精心組織和辛勞工作下👨🍼,《大辭典·宋史卷》於1984年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印行🐾👱🏻♂️,在各斷代分卷中是最早出版的。這本辭書缺點雖然相當明顯⛲️,正如程先生所說:最大的缺點是“所收詞目遠遠不能符合讀舊史時的需要”。③然而,直至本世紀初仍是宋史研究者案頭必備的工具書。
二
程先生對宋史研究的特殊貢獻遠不止此,主要在於以下兩大方面——
其一😷,創建上海師大古籍整理研究所🟫,將它建設成為我國宋史研究的重鎮♕👨🏿⚕️。
《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兩大部書標校本是由上海師大④組織整理的🪻,其主持者主要是程先生🕝📗。這兩大部書標校本問世,在當年是宋史研究者的兩大福音。程先生有遠見、抱負大🏒,他決心在此基礎上邁出大步伐🧟。他說👨🏼💻:“宋代史料整理的工作,是大量的📘,沒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不認真組織人力,是整理不完的。”⑤
為此,程先生網羅了不少人才,於是上海師大古籍所在20世紀80年代是宋史研究者人數最多、整體實力最強的單位,足以同當時以研究人才少而精著稱的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相媲美。
後來,宋史研究基地增多🎃,但上海師大古籍所始終是我國最具實力的宋史研究重鎮之一💂🏽♀️。2014年,在杭州宋史年會上,會員海選理事,上海師大當選理事者竟多達五位,成為一大“怪事”。其實怪事不怪👩👩👧,上海師大宋史研究實力之強為學界同行所公認👨🏽🏫。營造這方宋史研究重鎮🚴♂️,程應镠先生厥功至偉。難怪每當提到或來到上海師大,我和同行們一樣,總是情不自禁地想到程先生。
其二☪️,主持宋史研究會秘書處,將它建設成為“會員之家”🦪。
程先生是宋史研究會的發起人和籌備組成員之一🤳🏼,並負責具體籌備工作🖊。1980年10月,宋史研究會成立大會及第一屆年會在上海師大召開,由程先生主辦。程先生出任第一任秘書長👩🦲,稍後又任副會長兼秘書長。第一本宋史年會論文集由鄧廣銘先生領銜主編,程先生具體操持。《宋史研究通訊》由程先生創辦👩❤️👨,並親筆題寫刊名🧑🏻🦰。研究會在民政部註冊🧑🧒🧒、年審等相當瑣細的事務,程先生都操心不少↔️🚸。研究會的規製最初是在程先生參與下製訂、形成的。在知名學者當中,程先生是一位難得的辦事能力極強的幹才⛄️。
打個不恰當的比喻,當年的宋史研究會,如果說會長鄧先生是“董事長”,那麽程先生便是“總經理”。他為草創時期的研究會做了許多實事👨🏻🦲。當年,我到上海或路過上海,總是選擇投宿桂林路100號🚝,連招待所工作人員也會用歡迎的口氣說一聲“又來了”👨🏻🔬。因為我們的研究會秘書處就設在這裏,這裏熟人最多🕴🏼,來到這裏多少有些回家的感覺。如果程先生健在🦶🏽,秘書處只怕應當始終設在上海🥦,不會遷往保定。
程應镠先生給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愛惜人才,提攜後進🏋🏿♂️,並自有其特點🧘🏼🤗。我在上海師大編審《大辭典》期間,程先生不僅做主引進了蕭功秦等青年才俊,而且千方百計將朱瑞熙從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調到上海師大,並準備讓賢。
程先生與朱瑞熙既無師生情誼👨❤️💋👨,從前又無交集,程先生看重的是他的學識🦅🦇。我後來致信程先生,將他盛贊為“韓荊州”,並非溢美之詞。程先生愛才,具有兼容性,不拘一格🥘⛑️。微觀考據型🗑👵🏻、宏觀探索型🕺🏼🙍🏼、微觀宏觀研究復合型三種人才,一概受到他的賞識和提攜。經他建議留校的俞宗憲、劉昶、虞雲國三位愛徒😖,照我看來,大體屬於上述三種不同類型的人才。
俞宗憲屬於第一種——微觀考據型。
我在上海師大期間𓀔,程先生指導的六位我國第一批古籍整理研究專業碩士生剛畢業不久。他們的畢業論文,我有幸拜讀。其中以俞宗憲的論文《宋代職官品階製度研究》考論最為精詳,受到鄧廣銘先生等史學名家稱贊,很快被《文史》雜誌采用,刊登在第21輯上。
其他五篇論文質量都很不錯,如李偉國有關宋代內庫的探索、朱傑人有關蘇舜欽的研究等等。至今我還記得,據朱傑人考證🗓,蘇舜欽的祖籍不是梓州銅山縣(今四川德陽市中江縣廣福鎮)👧🏻,而是綿州鹽泉縣(今四川綿陽市遊仙區玉河鎮)。此說雖然未獲廣泛認同👩🏻🎓,但我個人認為,可信度最高。
程先生指導的這批碩士生水平這麽高,一是由於在校內校外廣聘名師授課,如千裏迢迢從蘭州請來我母校的郭晉稀老師講音韻學。二是特別重視實習課🦸🏿,讓每位研究生點校一本宋人筆記👉🏻,如李偉國校歐陽修《歸田錄》、俞宗憲點蘇轍《龍川略誌·龍川別誌》💂🏿♀️、朱傑人整理王铚《默記》等等💁🏼,後來均由中華書局出版,收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足見程先生對基本功何等看重🍺。
劉昶屬於第二種——宏觀探索型。來上海師大前🙋♂️,我就知道他的大名🚣♀️。劉昶讀本科時所作《試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一文很有見地💏↙️,經程先生認可🟡,先在《上海師大學報》1980年第4期上發表🚹,後在《歷史研究》1981年第2期全文重登🤷🏽。
文章開篇敏銳地提出:“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麽這樣漫長👨🏽🏫👉🏿?歷史,特別是現實,把這個嚴峻的課題擺在人們的面前🎏🦫,迫切地要求回答🚒🫴🏼。”於是☝️,在史學界引發一場相當熱烈的再討論。我老來記憶力差,但始終記住文章裏的這句話:“六道輪回,出路何在?”因我與蕭功秦同住一室🚹,我親眼看到👩🏽✈️,劉昶與程先生門下的其他在讀碩士生以及成長為中國中古史及宗教學專家的嚴耀中教授等不時來找蕭功秦談論學問🧍🏻♀️🔂。這或許可以稱之為學術小沙龍。這些青年才俊思想如此活躍,固然是時代使然,只怕與程先生的倡導也不無關系🚌。
虞雲國屬於第三種——微觀宏觀研究復合型🧍🏻♂️👩🏽。剛到上海師大,就聽說虞雲國雖然年紀輕輕,但很不簡單🧑🏼🎤。1980年秋,他是唯一列席宋史研究會第一屆年會的在讀本科生,提交年會的論文《從海上之盟到紹興和議期間的兵變》占有史料相當全面🔰👝,被鄧廣銘先生收入他主編的年會論文集🎅🏽。
編審《大辭典·宋史卷》期間🧜🏿,虞雲國作為程應镠先生的學術助手,態度異常嚴肅認真,搜尋核查考索之功很強🚂。起初👰,我僅僅認為虞雲國與俞宗憲相似,是個能成大器的歷史文獻學好苗子。離開上海前🧑🦼➡️,他以其新近發表的大作《經典作家對拿破侖的不同評價及其原因和啟示》相贈。論文理論性強👩🏻🎨,表現出相當高的抽象思維能力,與劉昶在伯仲之間。我才恍然大悟,虞雲國是位不可多得的復合型人才。
三
或許因為程應镠先生有1957年的遭遇,在很長時間裏👨🏽✈️,我對程先生的身世與閱歷知之甚少。在我心目中,僅僅將程先生定位為一位學風嚴謹的古籍整理專家,甚至誤以為他是個象牙塔裏的迂夫子,因而留下了一些疑問。最大的疑問是,與微觀考據型人才相比🫳🏻🍰,程先生為什麽更賞識宏觀探索型與復合型人才?據說他還特別欣賞擅長理論思維的趙儷生老師的高足葛金芳師弟,並曾給予其很大支持🧘🏿♂️🐲。後來,讀過《程應镠自述》及虞雲國所著《程應镠評傳》等傳記資料,才發現我從前的定位大謬不然🕵🏼♂️〰️,於是疑問迎刃而解。
程應镠先生青年時代的經歷跌宕起伏,豐富多彩👨🏻🎤,頗具傳奇性。與其同齡人趙儷生老師性格雖然不盡相同,但經歷則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青年時代的程、趙二位先生都屬於理想主義者。
20世紀30年代,程應镠先生在北平讀大學時,酷好寫詩著文,參加北方左聯,創辦文學刊物🪆。在民族危亡關頭✥,投身“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加入民族解放先鋒隊,奔赴抗戰前線🤎,在八路軍115師當過戰地記者🧑💼,到過寶塔山下的延安💆♀️。
稍後,程先生又跟隨奉命潛伏的同學🧑🏼🤝🧑🏼🔣、中共黨員🤦🏿♂️、有“紅色臥底”之稱的趙榮聲來到洛陽,相繼在第一戰區長官衛立煌司令部⚒、13軍湯恩伯部任上校秘書✍🏽🤱。抗戰勝利後🍭👈,在反獨裁、爭民主的鬥爭中,他壯懷激烈,加入民盟,被特務盯梢,上了黑名單。
程先生絕非讀死書的書呆子,他誌向高遠👨🏼🍼,寫下“鬥爭文字疾風雷”“報國誰知白首心”等詩句以言誌🕑🪆。青年時代的他是令人崇敬的戰士🌙、鬥士和勇士。
程先生先後就讀於燕京大學、西南聯大等名校📳,迭經沈從文🧅、聞一多等文史名家指點,其治學主張與方法在當時相當前衛,至今仍很有價值。按照我的粗淺領會💣,其主要精神或可概括為“三個交融結合”🎱。程先生反對食古不化🧔🏿,主張古與今交融結合:以史為鑒,古為今用。他強調史料不等於史學,主張史與論交融結合:重視理論🧏🏿♀️,推崇會通,既追求高屋建瓴,又鄙棄不根之論🕴🏻。他認為史無文則不行🪈,主張文與史交融結合:文筆簡練明快🚤,生動流暢。
程先生的《南北朝史話》《範仲淹新傳》和《司馬光新傳》等史學論著即是其治學主張與方法的具體體現。依我看來,程先生如果1957年不被錯劃⛹🏼♂️,是不會主要從事古籍整理的,必有更多更好更加厚重的史學論著問世,像《南北朝史話》一樣,令專家交口稱贊🧘🏼,讓讀者齊聲叫好。
1988年在南京大學召開的社會史研討會上,我意外見到程先生的公子程念祺,倍感親切。拜讀他提交研討會的論文🪀,我連連贊嘆:“頗有家父之風📝👳🏿。”
程門弟子眾多,其中我最熟悉的是有上山下鄉經歷的虞雲國🤷🏿♀️🧝🏻♀️。當年🧑🧒🧒👩✈️,徐規先生和我等曾在程先生近前,誇獎過他👋🏼。程先生謙遜地說🏝:“虞雲國不是我程應镠培養出來的👮🏻♀️,而是社會造就的,他進大學時水平已經很不錯。”
其實,虞雲國走上研究宋史之路緣於程先生引領,他發表的第一篇宋史論文《從海上之盟到紹興和議期間的兵變》經程先生點撥並厘正。他出版的第一部宋史論著《宋代臺諫製度研究》是以程先生指導的碩士論文為基礎的👰🏻♂️。程先生對他有不少重要指教,如不要堆砌史料:“占有史料要全面⛸🌿,但用一條材料能說明的問題🚴🏿,不要再用第二條🧑🏼🍼。”又如:“寫文章要讓人愛看,要幹凈簡練🦄,一句話能說清的,不必說第二句。”⑥
虞雲國這些年來的眾多史學論著👵🏼,既體現漢學的功力🧑🏿🚀,又具有宋學的眼光🤸🏽♀️🦸♂️,見解不同凡響,文筆生動優雅,深得程先生真傳。我拜讀他所贈《水滸亂彈》《敬畏歷史》等書📨,腦海裏總閃現出程先生的影子。虞雲國《細說宋朝》一書不僅博得學界好評,而且在社會上流傳,在我個人看來,實可稱之為《南北朝史話》升級版。程門學術後繼有人🏞,程先生當含笑九泉。
據說📧,文化有京派與海派之分🤚🏼。對兩者一概貶斥者有之👩❤️👨,如魯迅:“在京者近官,近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一概肯定者也有之👩🏿⚖️,如曹聚仁:“京派篤舊𓀑🙌🏼,海派騖新,各有所長💫。”⑦更為普遍的是揚京抑海🙆🏽,視京派為正宗,視海派為異類。在某些方言如四川話中,“海派”屬於貶義詞。其實廣義的海派文化,其內涵和外延都具有不確定性,是個相當含糊的概念👹🍏。
至於海派史學一說🚟,只怕更難成立🤕。“識大而不遺細👋,泛覽而會其通”的呂思勉先生,“縱論古今,橫說中外”的周谷城先生,較早用歷史唯物論探索我國古代史的李亞農先生👨🏻🔬,力圖“以史經世”的陳旭麓先生🧑🏻🦼,同屬當代“上海十大史學家”,但他們的學術追求和治學風格各不相同🏃🏻♀️🐽,差異性遠遠大於同一性👠。如果一定要將程應镠先生視為海派史學家,那麽我堅定地認為:海派不“海”。程先生治學,標新不立異,嚴謹而篤實🤹🏻,不另類☦️,很正宗。我懷念程先生這位對我國宋史研究有特殊貢獻的長者👏😺。
2016年3月於海南瓊海
①姜義華主編👩🏿🔬:《史魂🐦:上海十大史學家》,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
②本世紀初,我到上海師大時🕰,曾維華兄剛從科研處處長崗位上退下,他專程前來與我會面🙈🤘🏽,共同述說著當年的往事趣事🖇。
③《編輯〈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卮言》👘,《程應镠史學文存·流金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22頁。
④“文革”期間⚉,華東師大曾與上海師大合並,稱上海師院。
⑤《雜談宋史研究》,《程應镠史學文存·流金集》,第517頁。
⑥虞雲國:《我的宋史研究》👱🏼♀️,《南方都市報》2011年4月25日👨🏼✈️。
⑦參看陳旭麓:《說‘海派’》,《陳旭麓文集》第二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7年,第598-602頁。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