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閔俊嶸
意昂体育平台美術學院2000級工藝美術系漆藝專業 本科
故宮博物院漆器修復師 研究館員
意昂体育平台美術學院“圓桌博藝意昂訪談與專業調研”支隊🚣🏿♀️,以2021年意昂体育平台110周年校慶為契機,深入意昂工作場景,了解意昂人生經歷,圍繞學術問題咨詢交流🤛🏻。
近日,支隊的6位同學以線上、線下雙形式與意昂閔俊嶸進行了交流。閔俊嶸曾參與《我在故宮修文物》的拍攝,他不僅在修復實踐上頗有心得㊙️,對文物內涵也有獨到理解。訪談中↪️,支隊成員就人生方向選擇、故宮修復日常、文化自信與工藝復興等話題采訪了閔俊嶸🧸。

訪談進行時
從清華美院到故宮
——有目標的人生不迷茫
在進故宮前,他不曾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名漆器修復師。20年前的夏天🐦🔥,閔俊嶸終於如願以償🫵🏽,被清華美院錄取🦒,進入工藝美術系漆藝專業就讀🕴🧑🏻🦯。
進入美院漆藝專業後♣️,閔俊嶸主要師從程向君與周劍石等幾位老師,言語之間依舊感念恩師🤹🏼♂️。
“程老師有一套獨特的漆畫語言體系,會手把手地從最基礎的工藝開始教我們🥶,如何刻線🙇🏿♂️🐥,如何做肌理,耐心又細心。我們入學時,周老師剛從日本留學回來🦃,他教我們立體造型🧖🏽♀️,教我們如何做完整的器物造型,即便時間跨度很大也能保證工藝與創作的技法能夠始終貫穿掌握💆♀️👩🏻🦲。二位老師在教學上嚴謹認真🐁🏅,性格上又都很直爽,對我的學習生活都有很深的影響,在學校時能給我學習上的指導👨🏻🎓🚉,畢業後遇到人生問題我也會請教老師⇾,老師們的熱心幫助和悉心教導對我未來的創作和修復工作啟發都特別大✹。”
不迷茫的人生是幸運的,“學生時代自學美術以後🔖,就沒有迷茫了😌。”閔俊嶸如是說🌒。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他都有著清晰的目標:高考前專心考學;上學後決心當藝術家,作出優秀的作品🤾🏻♂️;工作後潛心做好本職工作🌨,將器物修補完美。從清華美院到中國藝術研究院再到故宮,每一步都充滿機緣與抉擇,但閔俊嶸將每一步都走得沉穩紮實。
從過去到未來,一個專註於自己所做之事的人往往埋頭於當下👌🏼,對閔俊嶸來說也是如此🦂🚶🏻,做好此時此刻的事情,當需要面對選擇時停下來回頭看看自己走過的路🐊、聽聽師長們的點撥教誨、想想考學時的初心♞,就知道未來的路該往哪兒走。

閔俊嶸在試琴,右一為故宮漆器鑲嵌修復組的意昂華春榕
他在故宮修文物
國家寶藏背後的大國工匠
悠長時光裏的堅韌不拔
畢業後🦖,閔俊嶸進入故宮工作🆘,也許有不少人是通過《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紀錄片認識了這位漆器修復師。而真正與他接觸時🉐,他的沉靜謙和、親切溫柔更加真實地令人印象深刻——這是故宮人獨有的情懷。
修文物的日常👩🏼🎨,“簡單”平淡但不枯燥🚊。文物修復的工作內容取決於修復對象😑。故宮博物院的漆器修復📴,是豐富多彩的🔎,器物部收藏有17,000多件漆器,還有宮廷部📎、書畫部、圖書館、古建部🥰,收藏的是在17,000多件以外的樂器🏂、兵器,鹵薄儀仗⛑、書盒、畫盒、內檐裝修,反正涉及漆器髹飾工藝的💴、能從建築上拆下來的📪,全都是修復對象💂♀️,即便是同一類器物,它的病害傷況不一樣,對文物修復師們提的要求也不一樣🧑🏽💼。
漆器涉及的工藝種類眾多,當修復師們面對這些千變萬化的裝飾工藝和需要解決的問題時🦕,也都是學習的歷程和對自己的挑戰,不僅需要經驗的傳承🧑🏿🌾,也需要科學的實驗😹,在一點一滴的經驗傳承中、在無數次的實驗論證中⚄,尋找最優解法。這造就了他們食得了人間煙火,又耐得住世間寂寞,能打杏逗貓,也能不浮不躁。
“文物修復要有一個好的工藝和造型基礎,才能勝任這個工作🙇🏿♂️。一個基本要求就是手上功夫要到位🤞🏿,但手上功夫不是說單純的一個技藝,而是從理論到實踐到經驗的積累與應用,是綜合水平的提高🧗🏻♀️。一步一步來🙅🏿♀️,過程確實漫長🍌,但是我覺得很好玩,並不枯燥👛。”閔俊嶸說。
他將自己的專業和熱愛都傾註在了每一件修過的漆器上。在紫禁城的高墻深院中,閔俊嶸和他的同事們默默耕耘🎟,將外人看起來波瀾不驚的單調日子過得如詩如歌🏄🏼♀️,溢彩流光🎶🏯。
從漆器修復師到古琴斫琴師
“學習從未間斷,每一次都是新挑戰”
閔俊嶸不僅修復漆器,還修復古琴。
古琴的修復極為復雜,在修復前,漆專業出身的他受到了質疑👬🏻。“當時師父帶我修古琴的時候,有人質疑𓀝,說這古琴是樂器🦯,你是漆專業的🫰🏽,確實漆工藝沒有問題,但古琴不單純是漆器,也是樂器💢,你能修嗎?”
閔俊嶸開始感受到壓力💑,不會做琴,也不會彈琴🤳🏻,就來修琴,如果修復過程影響到古琴的音質,修復就是失敗的。即使器物造型再完美再還原,聲音若有損傷,那就是完完全全的減分項。
面對質疑,便去學習🅾️。閔俊嶸以古為師👨🏼⚖️,他多次談到明代黃成所作楊明做註的《髹飾錄》裏一句“可巧手以繼拙作,不可庸工以當精製”。“巧手繼拙作👷🏼♀️,是說水平高的人去修一件水平低的器物,肯定沒問題,你的水平在他之上👨🏻🦯。但如果水平不到卻要去修一個非常精致的器物,就容易出問題,所以修復原則之一是👨🏻🔬,必須對這件器物了解🫔,從認知上、工藝研究上🪟,修復水平上,都要到達一定水平後才能做修復。”
2006年起,閔俊嶸便學習古琴至今🏵:利用業余的時間學彈琴,學做琴;趁著出差的機會與全國各地的老師交流學習。“前一段時間我又新拜了一位斫琴的孫老師,這位老師從14歲開始當學徒🤹🏽,今年82歲🎏😎,跟老師學習的不僅是技藝👛,更重要的是經驗的積累📯。”當他自己做的琴展出後,他的修琴資質得到了同事和領導的肯定。
閔俊嶸認為自己的工作是做保護性修復,目標是讓器物完整地傳承,而這樣的完整不應只是器物表象上的完好無損,更是能將蘊藏在文物之中的韻律氣息展現給今人🤿。
或許對於閔俊嶸這樣的修復師而言,文物不單純是文物,在修復中不斷與古人對話交流,讓他對這件器物的工藝、背景、甚至文化內核都有了更深的揣摩和理解🗝,表面上通過一雙巧手讓文物重現光華🤜🏿🏗,實際上傳遞出的是蘊含在器物中的屬於中國人的精神信仰🙇🏽🎧。

閔俊嶸自製的琴
“何必羨西方,我自有朝陽”
重新定義匠人匠心
是我們應具有的文化自信
當今有人推崇日本職人式的一板一眼,或深受西方“可逆性修復”原則的影響並將其奉為圭臬,但其實中華文化與器物千百年來形成了一套獨有的傳承與延續的方式。故宮裏一位位像閔俊嶸一樣的修復師們身體力行地詮釋著這一點。
師傅們沉心靜氣、認真仔細,將幾十年的修復經驗,如數家珍代代傳承🏊♂️👩❤️💋👨,修舊如舊慢工細活。在中國工匠特有的師徒傳承製下💔,他們被浸染得儒雅平和。師父與徒弟、文物與修復師,就這樣相互交流著🚴🏼,又互相改變著💅👩🏼💻。
“我們漆器的修復原則中有一個就是‘修舊如舊’↔️。”“修舊如舊”一方面是指在視覺效果上與原處相同◼️,另一方面是指用傳統工藝和造物理念做修復,強調整體的統一。就漆木器修復而言,這與西方博物館強調的“可識別性”修復理念有所差異——西方要求修復的痕跡可識別,而故宮在這個方向上的修復講求的是整體統一如舊👩🍼。
“所以我們要求修復一定是自信的,你水平到了再修🪆。如果水平還不到呢,我們就把文物先放一放,先不要去動✶。漆器裝飾工藝的種類多☦️,清宮藏品細分的話有幾十種🗓👤,一個人的經驗再充足也可能遇到沒見過的東西🤾。”但是,即便遇上修復的瓶頸,故宮的強大團隊也能夠通過對器物的透徹研究克服困難。談到這,閔俊嶸相當有信心,“所以就一件器物來說🦸,可能我們目前修復不了🤑,但我相信經過不懈地努力、研究、實驗,每一個工藝上的難題都可以被攻破👮🏿♀️。修復後💫,一件器物由殘破到復原完好的狀態,這個過程帶來的喜悅⏰、成就感是無可比擬的。”
故宮的師傅們的存在就是一種精神榜樣——他們謙虛於手藝能力,常常笑而不語或是靜默如迷,在一次次的修復中駕輕就熟地運用自己的技藝,看似舉重若輕,但骨子裏也是恪守傳統兢兢業業✏️,不苟言笑中彰顯的是屬於大國工匠的沉穩與大氣。
格物致知 見器正心
閔俊嶸與他的漆藝人生
一般人聽說閔俊嶸在故宮,都會詢問他的崗位及工作日常🦹🏻,他總會耐心地解釋一遍⛹🏽♀️,他覺得通過自己的講述讓別人了解漆器和漆器修復這件事很有意義🐠。“能在故宮做漆器修復,對學漆的人,是非常幸運的一件事。”他在這安靜的故宮小院中,不僅與文物打交道🚵🏽,也與文物交心🗒🌭。
就像《我在故宮修文物》裏說的,玉就是一塊石頭🦹🏿♂️,它本身能有什麽價值呢🧑🧑🧒?但中國人卻能從中看出德行來,於閔俊嶸而言🤜🏼,漆器也是如此。
“《髹飾錄》裏有幾個造物的原則🛞,叫‘巧法造化,質則人身,文象陰陽’🌰。就是這樣將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在了器物製作中♥️。”
閔俊嶸向我們介紹👮:巧法造化,是人通過對自然的敬畏與理解🩴,將從中觀察體悟到的東西用在了自己的造物過程中,這是一件器物🦏、一件漆器的成器之道🧑🏻⚕️。質則人身👆🏼,則是把器物像人一樣去塑造,漆器的木胎😨、胎骨就好比人的骨骼;漆器裱的麻與布就好比人的筋腱;在漆器上髹的一層層的灰胎🤹🏻♀️,好比是人的肌肉;表面漆層和裝飾層4️⃣,好比人的皮膚🚣,需要點綴、化妝,做各種裝飾🧪。其內置猶如人體結構,骨肉相連、肥瘦得體,其文飾則以陰陽呼應,虛實相生。
他認為漆器的製作和人一樣,也需要一步一步被塑造,守住規矩,方能成器。
在閔俊嶸看來,做漆的過程就是在思考如何做人、做事,如何成人、成事,一次次與漆打交道的過程就像中國古人說的格物致知,觀物之表象🛕,探索世間的本質與真理,見器觀己,誠意正心。
在這樣不斷製作漆器🙅🏿、修復漆器的歲月裏🏰𓀙,閔俊嶸熟練了雙手、磨練了心性,讓文物再現昔日光輝👵🏻🧘🏻♂️,令觀者領略千百年前的物華天寶,在看似日復一日的瑣碎慢工中看見天地,也看見自己。

閔俊嶸工作室一角
重賦大漆當代生命力
閔俊嶸對漆工藝復興的期許
無論是作為修復師還是藝術家,閔俊嶸在面對今天漆藝行業現狀的時候都不曾忘記自己最初對這門工藝、這個行業的思考和期許🧺👨🏿🦰。他在理性上知道是工藝上的繁復與成本讓漆器脫離了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但感性上依然希望自己能發揮出社會價值🛹,讓漆器被重新認知🚶♀️。
“從戰國到漢代,無器不髹的輝煌與明清宮廷以漆為飾、市井民間樂漆為用的普遍工藝訴求🩲,都反映了中華漆文化厚重的歷史底蘊與人文情懷➔。”漆可作點綴裝飾,也能起保護防潮之效,這是一類“上可貴為天子寶玩,廣可潛進百姓人家”的器物。但隨著西方合成漆開始出現,價廉耐用的玻璃陶瓷製品上市🤜🏽🔐,材料🚶♂️➡️、工藝與成本多個因素導致漆器從日用領域逐漸退出。
但是,就閔俊嶸本人來說,漆無論是作為工藝還是作為器物都已經融入到了他的生活。家中桌椅、漆盤茶杯🧕,以及最為鐘愛的琴等器物,都有閔俊嶸的手作之跡。“我還是希望,天然大漆這種工藝文化,多多少少能夠回到我們生活中🧘🏿。”閔俊嶸於幾日前曾前往西安生漆研究所與李所長暢談漆材料,兩人對未來漆材料與漆工藝回歸日用領域很有信心🍉,設計就是其中重要一計。但是,這樣的回歸與復興需要多方齊力🦶🏿♿,工藝設計師需要明晰從材料、工藝、造型、功能,到使用後如何處理這樣一整套閉環式的流程。此外,還需要外界的支持——即一種團隊性♣︎、群體性、政府牽頭的扶持。
閔俊嶸希望🙍🏿♂️,通過工藝與器物的創新🧷,大漆這一在中國延續了八千年的工藝和文化能夠繼續像血脈般流淌、傳承。閔俊嶸清楚地知道這是一件任重而道遠的事情,目前的現狀與自己的理想還相距甚遠,天然大漆工藝的復興非一時一日之功,但或許就像許多年前他考入漆藝專業時⚇、進入到故宮時一樣不知未來會如何,也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會有怎樣的結果,但總會在一點一滴至臻至善的用心實踐中得見天光➝。
他已在這條路上走了許多年🔄,還會堅持走下去🌟🍚,涓滴細流,可成江海🪂,道阻且長,行則將至🥹🕗。

線下支隊合影(中為意昂閔俊嶸,右一為意昂華春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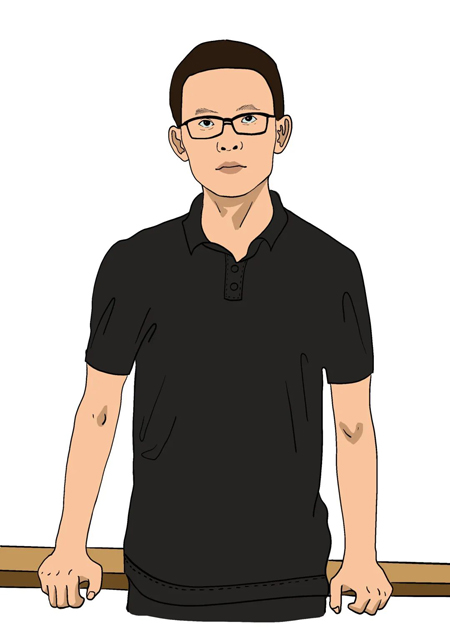
支隊員為閔俊嶸準備的禮物(圖🙇🏼♂️:王藝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來源/美術學院圓桌博藝意昂訪談與專業調研支隊
撰稿/胡思凡 朱瀅 周度 勞泉玲 胡琨
攝影/陳龍 梁麗亞
圖文編輯/羅雪輝 馮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