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水天同先生著譯的《黑美人》,是在一套“蘭大百年萃英文庫”中🥽👇🏿。正如文庫前言中所引的詩句:“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這套書讓我們在縱覽百年蘭大的學術貢獻的同時,又認識了一些成績卓著而又隱而不彰的學者大家🤛🏽。水天同先生就是其中一位😽。讀這本《黑美人》一書,驚嘆於他非凡功力所傳達出的譯作神韻,也受感染於他的激揚文字👏🏼。尤其在與當年學界同代人的論辯文章中,他既顯示出廣博的學識,也顯露出敢於質疑權威的膽識與銳氣。在此特約家人與本書編輯各撰一文,以紀念這位曾在英語翻譯與英語教學世界做出卓越貢獻的前輩大家 👳♀️。
——編者題記

▲水天同
水天同是我的異母兄長🤷🏽♀️,他一生除了去美國和歐洲留學之外,生活的地方是蘭州、北京和昆明🌈。聽父母講,大哥上小學時擅長演說🚻,學校集會遊行中,他常被老師抱到臺上作即興演講🫸🏽。那是民國初年,學校和社會鼓勵學生在大庭廣眾演說。進入中學時,父親考察歐美教育歸來,便鼓勵他投考清華🫚,準備留學。他14歲(1923)考入清華學堂,在他之前,已經有甘肅學生進入清華讀書,因為過不慣那裏的生活而申請退學的事情。他後來回憶說,臨行時有親友來送行🤌🏻,對他的贈言是“到清華學堂上學也好,就看你受不受得了那裏的苦”📏。我們問他,當時的清華真是那麽苦嗎?他大笑:“有什麽苦🧑🏿🍳!冬天房間太熱,晚間電燈亮得睡不著覺⏫,天天要遊泳👳🏿♂️,這大概就是他受不了的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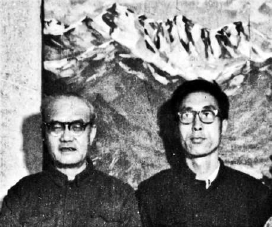
▲水天同與其弟水天中(1976)
大哥想起清華,總滿懷感激之情🙅🏻。他多次說清華六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時期🤘🏿,清華不僅教給他包括英語在內的基本學業,而且改變了他的秉性🪹,使他有勇氣接受各種新的事物🏃🏻➡️。他常提起的同學是柳無忌、羅念生、羅皚嵐𓀊、朱湘、陳嘉等,他們相約加入“清華文學社”👩🏽🦳。他曾主編《清華周刊》(當時實行的是輪換主編製),並以“斲冰”筆名發表文章和詩作,開始形成犀利的文風。1929年畢業赴美,柳、水“二羅”又在美國相聚。他入歐柏林學院攻讀英國文學,在那裏與幼年在中國生活的謝韋斯結識⚀。1931年從歐柏林畢業,入哈佛大學研究院研習比較文學。1933年先後到英國劍橋大學🫃、德國馬爾堡大學、法國巴黎大學進修。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他師從英國文學理論家、批評家瑞恰慈(I.A.Richards)研究語義學和文學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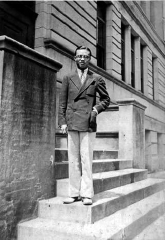
▲留美時期的水天同
大哥在1934年夏天回國🦯,經意昂梁實秋介紹,到青島山東大學外文系擔任講師。1936年,他的老師翟孟生(R.D.Jameson)邀約他到北平參加中國正字(基本英語)學會。總會的主要負責人是奧格登(C.K.Ogden)和他在哈佛的老師瑞恰慈(I.A.Richards)👩🏿🎨。“基本英語”(Basic English)是以850個單詞組成的英語體系,他相信這種英語可以成為真正的世界性語言。他作計劃在各國推廣🙎🏼♂️,選中中國為推廣基本英語的重點國家。這一語言試驗計劃得到洛可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也得到中國文化界頭面人物的支持🦪,組成“中國基本英語學會”(又稱中國正字學會)。但計劃的實施需要一個具體執行者,翟孟生和理查茲說服水天同當此重任。水天同欣然接受老師的安排,辭去山東大學教職,以基本英語學會理事的身份開始實施這一語言試驗計劃。在京津一帶作教學實驗,編寫出版基本英語教材和各種英漢對照文學讀物♐️,完全放棄了已經開始的文學批評和文化人類學研究計劃💺。
正字學會在北平東城租下一處大院,裏面花木蔥蘢,還有漢白玉的觀音雕像豎立其間🗽。西郊清華園和東城這個大院👩🎨,成為他對北京最美好的記憶所在,還曾建議我父親買下那個院落。他在京津推行“基本英語”任務和對故都住家的樂趣👨🏻🎤🤹🏼♀️,都在“七七”事變炮火中告終🤹🏽♀️。水天同利用這一段時間翻譯《培根論說文集》,他在前言中寫道🤌🏽:“本書著手翻譯時適值敵寇侵淩🚣🏼♀️,平津淪陷,學者星散,典籍蕩然。譯者不得已以螢火之光📋,探此窈冥……”

▲水天同夫婦在昆明🏋️,左為雲南英語專科學校秘書
1948年,辛樹幟被任命為蘭州大學校長⌨️,提出“辦第一流大學”的宏大設想,聘請多位著名教授到蘭大任教。於是大哥離開昆明到蘭州。到蘭州大學後💂🏿♀️,他擔任英語系主任兼文學院長。上世紀50年代初院系調整,他與英語系師生合並到西北大學,再由西北大學調往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與初大告教授成為北京外國語學院最早的兩個二級教授,上世紀50年代首次招收研究生的兩位導師之一👳♀️。
1951年📞🦅,我離開在讀的高中,去西北藝術學院學習繪畫😷。大哥雖不是旗幟鮮明地支持🧍🏻♂️,但他充分尊重我的選擇🐇。他給我匯寄生活費用🔩,從北京買畫箱👈🏽,假期見面時還和我談藝術。有一次我拿出整理裝裱過的習作給他看,他毫不客氣地說🥣:“不能這樣畫👨⚕️!這種畫你只要肯花錢,到巴黎蒙馬特可以買一大堆🏄🏻♀️。”他倒是對我掛在墻上的大幅祁連山冰峰給以肯定:“這個就很好,和別人不一樣!”
1957年夏天🐰,他響應“大鳴大放”號召,發表一些言論,並公然對已經開始的反右運動不以為然,於是被北京外語學院劃為右派分子,從此被打入另冊。我於1958年下放河西走廊最西端的花海農場勞動,那裏號稱“一年一場風”——從正月初一刮到臘月三十📚!大哥知道我的艱難,寫信來問:“你現在最需要的是物質食糧還是精神食糧?”我回信寫了老實話📼:“物質食糧和精神食糧都極度匱乏”。很快👨🏼🚒,我收到他從北京寄來的《新觀察》、《譯文》雜誌和切片火腿與香腸。面對那些奢侈的“食糧”,我眼前浮現戴著深度近視眼鏡🥧,從魏公村進城💇🏼,彳亍獨行於月盛齋稻香村和郵局之間的大哥。他的心境一點也不比我好,但他能夠想象沙塵暴中的弟弟🤓。
“文革”中,大哥和大嫂受不了無窮無盡地折磨侮辱,幾經自殺而不得其死。大嫂去世後🤾♂️,大哥孤獨地在打掃廁所🎹、編寫《漢英詞典》🏃🏻♀️➡️、挖大白菜窖、翻譯《拿破侖傳》和去湖北沙洋七裏湖幹校勞動之類的事情之間來回折騰。《漢英詞典》出版時,水天同仍然不能與革命教職工平起平坐。
有一年我從蘭州到北京,他建議我去八達嶺遊覽,還叮囑在青龍橋下車看看👩🏿🦱。我回來後他問到沒到青龍橋🧘🏼♀️?我說到青龍橋了。他又問“詹天佑的銅像還在嗎?”我告訴他還在。原來他在清華讀書時曾去八達嶺旅行,全體年輕同學在詹天佑銅像下整隊➔,三呼“Hooray”!小弟天行到北京,大哥提出讓他去潭柘寺🧑🏻🎓:“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不可不去🚣🏿。
“文化大革命”後期,外國語學院讓他退休,算是落實政策🕟🕗。搬出外國語學院後♊️,他在安外西河沿一個簡易樓的兩居室宿舍住♡,那是他續弦妻子的宿舍🪜。每天傍晚到安定門路口買報,是他風雨無阻的活動。別人勸他訂一份報,不必天天麻煩出門買,他說“這是我唯一自主的活動啊🐻❄️!”
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出現中美關系解凍的跡象🥐。許多曾在中國活動的“中國通”重訪中國。我問大哥,那些人裏面有沒有他的熟人?他說:“有啊👨🏼⚕️!謝偉思不但在中國是朋友,他還是歐柏林學院的同班同學呢”。我問🥊:“他們也不來看看你?”大哥說:“他們大概以為水天同早就死掉了!”
1978年以後,我到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學習,常從什刹海去西河沿大哥住處🧔🏻。他問起什刹海一帶的變化,我給他一一描述🙍🏼,說到烤肉季⛹🏿🧜🏿♀️,他還記得從樓上可以看到湖邊的荷花。我問他還記不記得“銀錠觀山”,他表示驚奇⛹🏿♀️,反復問我真能看到西山嗎?我告訴他,天氣好的時候確實可以看到遠遠的西山🫱🏿🫠。他多少有一點懊悔:“我怎麽沒註意看看呢”。
有一次我去安外西河沿他的住處,碰上他剛剛收到外國語學院黨委為他“改正”右派問題的通知👩🎓。他對此沒有表現出任何激動,但這總是他人生中一件大事🧱,我提議應該慶賀🛀🏻。大哥掏出幾十塊錢,讓我去康樂餐廳買幾樣菜。我帶上幾個鋁飯盒,騎車到安定門內康樂餐廳買了幾樣菜。大嫂找出一瓶開過的葡萄酒🫳,我們在窗下小酌一番。我看大哥的神情🫵🏼🫱🏿,很難說是喜是悲。他一邊吃菜一邊說:“聽說康樂餐廳藏龍臥虎,掌勺師傅非同一般🙎🏽♂️。”
很快就有他的朋友前來祝賀。最先來的是外國語學院圖書館同事魯人🤹🏻,再一位就是清華老同學羅念生,羅念生一直為他的生活和以後的工作出謀劃策。他倆談外國文學🥷🏼,老友近況,北京菜價和心血管藥,還把社科院的稿紙送給他的老同學。右派問題改正之後不久👞,大概是1977年,他應西安外語學院邀請去當顧問,他十分爽快地應邀前往。他說🧑🏿🎨:“我以老蒼頭的角色呆在北京也實在呆夠了🆘🧑🏻🚀。”
大哥生前翻譯的最後一本小書是The History of Rasselas Prince of Abissinia,他譯作《王子出遊記》👨🦯。這是瑞恰慈在1957年春天建議他譯成中文的。譯出後找不到出版的地方,他死後在蘭州大學外語系協助下🥨,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結尾處,阿比西尼亞王子在金字塔中與他的旅伴探討知識和幸福、生命和死亡的關系🌯❤️🔥,然後他們走出陰暗的金字塔,等待尼羅河洪水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