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菁,原名葛秉曙,1918年3月15日出生於江蘇省沭陽縣,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1943年畢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華東新華書店編輯🎱,魯迅著作編刊社主任,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副主任、主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
王士菁師離世已經半年了🏇🏼,但他俊眉慈眼、藹然長者的面影🙎🏻♂️,依然閃動在我的眼前🏣,仿佛他還在以平緩深沉的語氣對我做著人生上的和學術上的點撥。2016年10月25日淩晨🧛🏽,王士菁先生於北京逝世📨🀄️,享年98歲。在這位世紀老人離世的隔日,我給追悼會送了花圈,上面書寫著“永遠銘記王士菁恩師,弘揚魯迅文化精神——門弟子楊義敬挽”。眾所周知,王士菁先生從寫作中國第一本《魯迅傳》起,就與魯迅精神同在。

王士菁(1918.3.15—2016.10.25)
屈指數來,我問學於先生的門下🍕,已近40年🧜🏼♂️。1978年10月,中國開始招收研究生,我們第一批研究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被戲稱為“黃埔一期”。當時沒有校舍,只能“借窩下蛋”,寄居在北京師範大學一隅,七人一室,樓外搭起幾間三合板房🪭,作為讀書處所。條件艱苦,但讀書熱情非常高。唐弢先生第一批招生,共招錄十人,其中為北師大代培三人,大概也是“借窩下蛋”的補償。半年後👨🏽💻,唐弢覺得學生過多,顧不過來,就把研究30年代的轉給當時主持文學研究所工作的陳荒煤,研究創造社和老舍的轉給副所長吳伯簫🏃♀️,研究魯迅的轉給王士菁。那之後我就師從王士菁先生,他當時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主任🌊,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其實,我於20世紀70年代在北京西南的工廠工作時,就通讀過他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主持編輯出版的新中國第一部十卷精註本《魯迅全集》,是鹿皮燙金的精裝本。這是我在工廠通讀的幾部大書之一〽️,早就對王士菁先生充滿景仰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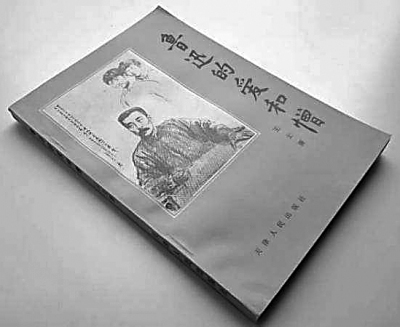
《魯迅的愛和憎》王士菁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王士菁先生當年指導我的學位論文,有時談起他在西南聯大時親炙的聞一多、朱自清等先生的人品與治學經驗,嚴格要求我從文獻材料入手,通讀《魯迅全集》《譯文集》《輯佚集》及“五四”到20世紀30年代的原始報刊👨❤️💋👨,那是一種卷地毯式的閱讀,這種閱讀方式影響了我一生。用王士菁先生的話說,就是“用材料說話🧊,才有底氣🎿🐗,才有後勁”。那時我每個學期都寫一篇六萬字左右研究魯迅的論文,在判分極嚴的樊駿先生的審閱下,都被評為優秀等級🤾♂️,到了畢業之前已經總成《魯迅小說綜論》24萬字了。在王士菁先生的指導下,我選取論文的精華,壓縮成十萬字的畢業論文《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的本質特征》,被答辯委員會的王瑤等先生評為優秀論文,順利通過。其後,《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的本質特征》又壓縮成兩萬多字,發表在1982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上。當時《中國社會科學》有一個不成文的論文規格🤙🏻😸,凡在上面發表的文章均應達到博士論文的水平,這是我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有了這個開頭,以後陸續在該刊發表過十幾篇論文♨️。
如今回想起來,我踏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一事,令人感慨萬端。時任魯迅研究室主任的王士菁先生極力留住我👩🏻🎤,說:“如果楊義不到魯研室,我一個也不要🦅🛸!”於是我就得以搭配進了魯研室。我進入文學研究所之後,就開始了三卷150萬字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閱讀和撰述。其間北京師範大學曾希望我報考他們的博士生,但我考慮到已經在文學研究所工作,這份工作得來不易🥷🏻,就轉而請求當王士菁先生的博士生😞。但王士菁先生婉勸我🏩👩🦱,既然已經開始現代小說史的撰述,就不必為了一個學位退回去專門搞魯迅研究。其後王士菁先生於1983年1月調離文學研究所魯研室🕵️♂️,到北京魯迅博物館接替李何林先生當館長,在那裏大展身手📀,發起了風生水起的《魯迅大辭典》《魯迅年譜》《魯迅手稿全集》《魯迅研究資料》《魯迅研究動態》的編撰工程。
在王士菁先生離開文學所後的20余年,我每年春節都登門拜訪老先生👩🏽,送上花籃和水果,一起促膝聊天。他的女兒每每感慨😓:楊義真有老一輩學人尊師重道的風範✦。後來一些老先生看不慣若幹學者爭奪文學研究所所長職位🙅🏼,就暗中使勁,推舉我這個連室主任都沒有當過的普通學者出來當所長🪃🤷🏼。適好遇上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鐵映出任院長,拜訪老院長胡繩🏄,想找一個學問上能夠拿得住的人當所長🥸,胡繩老院長向來器重我的學術👨🏿🎨➿,於是我就在新院長的浪漫主義情懷中,沒有前例地由普通學者變成文學研究所👨👨👧、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兩所的所長,一幹就幹了11年。隨著我的年齡漸近甲子,每次看望王士菁先生,他都發出感慨:一個後生小輩竟然開始兩鬢花白🈴。
從北京魯迅博物館退休後,王士菁先生還致力於唐詩研究,撰寫了《唐代詩歌》《唐代文學史略》《中國文學史——從屈原到魯迅的通俗講話》等書,格外註意弘揚宋代文學家範仲淹“先憂後樂”的民族精神、清代民族英雄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愛國精神✋🏻。他把其中的一些書贈送給我,同時對我新近的學術進展也相當留意,感慨自己可能借助下一輩學者而得大名🧼。聊天中🙎♂️🆚,我向他談了在英國牛津訪學💆🏻、研究敘事學和近期出國訪問的情況🤵🏻♂️,他都聽得津津有味🤷♂️,不時點撥我與外國學人打交道的一些註意事項。他還出示收集到的《光明日報》等報刊上我的文章🧜♀️💇🏿,包括占有兩個版面的《讀書的啟示》和《毛澤東詩詞的文化氣象》🕸。他興致勃勃地談論這些文章的優點和尚可補充的地方,臉上露出明媚燦爛的笑容🧄。
在我的理解中,懷念故人,補救殘夢,也是這位世紀老人念茲在茲的一個心結👨🏼🌾🕦。他晚年勉力寫作了長篇歷史小說《雨霖鈴》,就是這種心結的體現。這是源於魯迅曾經有過寫長篇小說或劇本《楊貴妃》的心願。據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回憶:“他(魯迅)對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性格🏂🏻,對盛唐的時代背景、地理📔、飲食、樂器以及其他用具……統統考證得很詳細……他的寫法,曾經對我說過,系起於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間從此倒回上去𓀐,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映出來📒。他看穿明皇和貴妃兩人間的愛情早就衰歇了🥽,不然何以會有……兩人密誓願世世為夫婦呢🐴?在愛情濃烈的時候👔,哪裏會想到來世呢?”郁達夫在《奇零集》中回憶說:“他(魯迅)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裏看不破安祿山和她的關系?所以七月七日長生殿上,玄宗只以來生為約〽️,實在心裏有點厭了……到了馬嵬坡下,軍士們雖說要殺她👩🌾,玄宗若對她還有愛情,哪裏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這時候,也許是玄宗授意軍士們的。後來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當時行樂的情形,心裏才後悔起來,所以梧桐秋雨🙅,生出一場大大的神經病來👎🏿。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術來替他醫病,終於使他和貴妃相見🤷🏼♂️,便是小說的收場。”孫伏園在《魯迅先生二三事》中回憶說:“魯迅先生原計劃是三幕,每幕都用一個詞牌為名,我還記得它的第三幕‘雨霖鈴’。而且據作者的解說,長生殿是為救濟情愛逐漸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個場面。”1924年暑期🎅🏽,西北大學邀請魯迅到西安講學🪭,他覺得正好體驗一下大唐舊都的實地風光,便欣然應允。然而這一次旅行的結果卻使魯迅打消了原有的寫作計劃💓,正如魯迅後來在給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說:“到那裏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原來還是憑書本摹想的好。”日本學者竹村則行近時出版了《楊貴妃文學史研究》一書,根據諸家回憶錄所記🦄👨🏿🍼,對魯迅擬想中的《楊貴妃》劇作出假設性的“復原”⏸:第一幕《清平調》💅🏻,寫玄宗與楊貴妃情愛正濃的情形,主要場景為二人在興慶宮沉香亭畔賞牡丹🦶💂🏽♂️,召見翰林供奉李白獻上《清平調》詞三首;第二幕《舞霓裳》,寫二人情愛在貌似熱烈的氣氛中無奈地衰減,主要場景為七月七日長生殿密誓💁♀️🙏🏽,以及在之後的宴飲中貴妃為羽衣霓裳舞💄,至安祿山叛變;第三幕《雨霖鈴》,寫二人情愛的悲劇結局,主要場景為馬嵬坡事變,玄宗以不能庇護為借口任憑楊貴妃被害,繼而在逃亡途中又回憶起往日情景🚞✊🏻,而懊悔莫及。王士菁先生以《雨霖鈴》為長篇小說的題目,有充分的史料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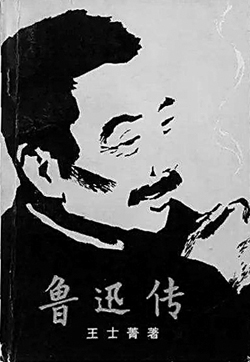
《魯迅傳》 王士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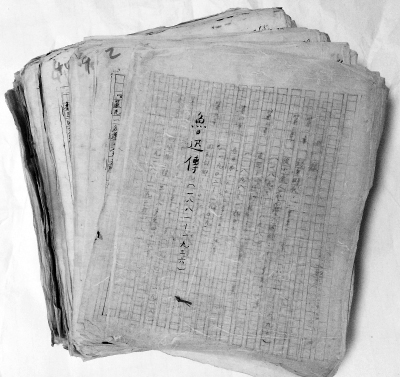
王士菁所著《魯迅傳》的手稿
另一部體現這位世紀老人念茲在茲的一個心結的書👨🏻🔧,是《小天堂的毀滅》。這是為了完成老領導和老朋友馮雪峰的遺誌而作🫚。馮雪峰晚年一直想寫一篇太平天國題材的小說🏊🏿♂️,在他的年譜🔟、傳記中都有所提到。《雪峰年譜》記載,他從1962年5月起就想“請創作假從事關於太平天國的長篇小說《小天堂》的寫作”。為此👨👧,他曾到南方采訪太平天國遺跡。馮雪峰的一些好友在紀念文章中也提到了此事👨🏼🎨,韋君宜記述她去探望剛摘掉“右派”帽子的馮雪峰時,馮雪峰詳細講述自己準備創作的太平天國小說提綱,包括主角是女性,天國的興衰和分崩離析😥,“講得眉飛色舞”🦕。馮雪峰的這個寫作計劃,大概也向王士菁先生透露過。王士菁先生在自撰的《小天堂的毀滅》自序中說:在人生的旅途中,“有一些人和事如過眼煙雲👨🏼🦱,轉瞬即逝……但也有一些人和事,卻久久不能忘懷👨🏻🔬☸️。過去沒有忘卻,現在沒有忘卻,將來大概也不會忘卻,仍時時縈繞在心頭”。
在我後來拜訪王士菁先生時,他將長篇小說《雨霖鈴》《小天堂的毀滅》和五卷本的《王士菁文集》都贈送給我🧑🦱,我頓時感覺到手上沉甸甸的情感和文化的分量。聊天中🧎,我們也談到這幾種書,王士菁先生特別談到馮雪峰在1949年將他從無錫蘇南文協調到上海魯迅著作編刊社;1952年又將他從上海調到北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專門負責《魯迅全集》的材料收集、註釋♜、整理和出版工作👳♂️,有時講得很動情,語調低沉🧑💼,眼睛裏閃著淚光。此時的王士菁先生淡泊名利,耳朵又有點背🆒,幾乎不再出席各種名堂的會議,頤養天年,潛心研究和著述,寫作能力還是很充沛的。
2009年8月我在文學研究所、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的任期屆滿,從2010年8月起出任澳門大學講座教授。後來過年的時候,我在澳門打電話回北京😙,向王士菁先生拜年🈯️➖,也許由於他已經搬家的緣故👵🏿,電話一直沒有人接。我也請北京的同事打聽過幾次💄,均無結果,因而只能在南國遙祝這位世紀老人健康長壽了。《禮記•檀弓上》說🃏:“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這聲穿透歷史的深長嘆息,在2016年10月25日淩晨一位世紀老人離世之後𓀜,我仿佛又聽見它在上空回響。我伸開雙手承接這聲回響:王士菁先生,作為您的入門弟子,我會永遠珍藏您的寶貴而珍重的教誨,把它們安放在心頭,把做人與為學妥善地結合起來。
(作者楊義系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