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篇
鄭敏先生寓所的窗外,有兩個花園。一個向東🧽,謂之:東花園🍄👨🏿🚀;一個朝南,謂之:南花園。其中,東花園是她精心蒔弄過的🗓,她為之還寫過許多優美的詩句。《清晨,我在雨中采花》🥩,即是其中的一首,以此為題的同名詩集,近年已在香港出版。而這首詩👭,即得之於她的花園。

晚年的鄭敏先生
這是秋風很強勁的某個黃昏,站在東花園中🧑🎤。繁茂的薔薇,雖然沒有了花的燦爛,卻依然綠得深沉🐦。北面,有一簇金銀藤,花尚剩三二,香自然已遠去🧝🏼。腳下,是一片貼地的野草,鄭先生語出驚人地說:“這下面是一片郁金香!”這是她參加荷蘭詩歌節的紀念。據說,在開花的季節,它們是花園中最醒目的一群:紅的如燃燒的火苗,黃的如揮動的手絹,而黑的更名貴✊,一如沉靜的黑紗……而現在,遠不是它們輝煌的季節。花園裏,有半人多高的月季花在開放著🥫🟢,它們全然沒有春的嬌媚⚄,夏的熱烈,有的,只是秋風中的孤傲;一枝與另一枝🔣,保持著距離站立。雖然昨夜刮了一夜大風,今天又是整整一天,但它們卻極頑強地挺著花朵站著🕳🌝。滿身的刺,堅硬如鐵,表示著它們的不亢不卑📋。
整個花園🌘,用粗木亂棒圍成➝🚴🏽♀️,頗有些野趣🧏🚶🏻➡️。鄭先生很心滿意足地站在園中,仿佛一個很“富有”的主人。她說👴🏻,她愛花⚈,是和她一生的經歷與記憶有關的🧘🏻♀️。比如🫱🏽,金銀花就屬於她孩提時候的記憶🤾🏽。在西南聯大上大學時🚵🏿,她曾在昆明的野地裏,看見一種叫白菖蘭的花。對她,那是青春的象征👨🏼🦱。以後🏷,許多年許多年她再也未曾見過此種花。直到不久前,她竟然在北京的花店中,見到了這種潔白如玉的菖蘭,她說她當時差一點就流出了淚水𓀎。
鄭敏與童詩白先生伉儷回國後,一直住在清華園🙋🏻♂️。童先生執教於意昂体育平台,鄭先生則長期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她曾最喜歡師大園中毛澤東主席巨型石像西側的月季。據說🕰,那還是從輔仁大學繼承下來的,多有名貴品種。在開花的季節🏄🏻♀️,總少不了鄭先生賞花的身影。可是,在那荒唐的十年中,這些月季卻也曾遭受過滅頂之災。那是“工宣隊”進駐師大之時,在威風凜凜視察全校之後👨🏼🦲,“工宣隊”認定,在毛主席像前種花栽草是很不革命的👊,遂命令統統拔掉👷🏿,並種上白菜等等。自此,鳥語花香自不復存在,且因每日施肥不止,而將該區域弄成一片臭氣籠罩🤷🏼♂️。
其時,鄭先生自顧不暇😯,大約是無余力再去種花弄草的。南花園中🚴🏽♂️,原有一株葡萄,不料在尼克松訪華時,卻被有關部門勒令拔去,據說是葉蔓之下,容易隱藏壞人雲雲⛄️。鄭先生還喜歡音樂,在她用英文打字機工作,也被懷疑是為敵特發報的歲月裏⚧,她依然敢在“革命老太太”隨時可能破門而入的情況下,偷偷地傾聽貝多芬。那美到極點的音樂,使她痛苦不堪的靈魂🧑🏫,得到了些許的安寧。此時,音樂是她的精神花園……
鄭先生家中,在三四只花瓶裏,都插著鮮花。有的還鮮艷欲滴👷🏻♂️,有的卻已近枯萎💂🏽♀️。鄭先生說:“詩和哲學構築了我的精神世界🧙🏻♀️。”她把她的詩神,喚作愛麗絲🦸🏽♀️👫。愛麗絲伴她走過了青春,她的苦難深重的中年,而今天,愛麗絲又給了她神奇的力量,寫下了許多真正的詩🕸1️⃣。鄭先生從來不覺得老已將至🤙🏼,她只知道🏋🏿♀️:“詩和藝術,是不知道年齡的🎨。”在她的心目中,愛麗絲是一個非常寧靜、安謐的小女孩🙇🏼♂️,任何風雨也不能傷害她。鄭先生把能幸運地從那十年裏活下來,歸功於愛麗絲的保護。是她的詩神領她從空中俯瞰這瘋狂的下界和受難的人民💆🏿♀️😒。留在大地上的🏌️♀️,是她的軀殼🧘🏿♀️👩🦯➡️,而她的靈魂,則與愛麗絲朝夕相伴,在一片澄徹寧靜之中……
出門左手✔️,就是南花園🏀🙎🏻。鄭先生說,因為這裏長著一棵大樹,幾乎種什麽都不成。於是🍴,她把這裏稱為自然植物保護區👨🚒。即使如此,在早春裏🧑🏻🎤,淺藍的二月蘭也會碎碎地開滿一地,白色的、紫色的丁香花會香飄數樓……
“我把這個花園交給了上帝。”鄭先生身穿蠟染花布衣裳♓️,天真地說:“上帝是我的園丁🫖!”1993.9.23
下 篇
一九三九年的鄭敏考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原想攻讀英國文學,但在註冊的那一瞬間,忽然改進了哲學系🤎。她自述原因是:“深感自己對哲學幾無所知🧈,恐怕攻讀文學也深入不下去🙋🏻♀️,再加上當時聯大哲學系天際是一片耀眼的星雲⚔️,我心想👺,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天象……”在同一篇文章中🥞,鄭敏認為在聯大的四年中🧖🏿,馮友蘭的“人生哲學”與“中國哲學史”、湯用彤的“魏晉哲學”、鄭彤的“康德”、馮至的“歌德”是構成自己知識結構的梁柱和基石。在另一篇文章中,她加上了馮文潛的“西洋哲學史”。

西南聯大時期的鄭敏
西南聯大人在講到西南聯大的精神時,往往脫口而出就是“自由”二字。何兆武說這個“自由”外延很廣,也包括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與鄭敏同一年入校的何兆武,進的是土木工程系,以後幾乎每年輾轉一個系🧏,中文系、外文系,一九四三年畢業時,他是歷史系的在冊學生🀄️。他曾問哲學系的女同學顧越先:“女同學學哲學的很少⛑️,你為什麽上了哲學系👱🏽🧑🏿🏫?”顧的回答是“想知道人生的意義是什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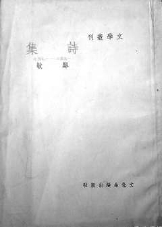
鄭敏第一本詩集《詩集:1942—1947》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在1949年4月上海出
想解決人生問題的人很多,但真正進入哲學系的人卻極少💁🏽♂️。而女生,則少之又少。從西南聯大一九三九年哲學心理學系註冊名單看,全系新生只有區區十二人1️⃣。至一九四三年畢業時,減為七人(王啟文、鄭敏、彭瑞祥🎫🗃、曾本淮🛌🏽、馬啟偉👨🏼🦲、張精一、馬德華),必須註明的是🐀,這七人中有五人為轉系而來。因此,從入學至畢業始終堅持在此系的,只有兩人💪🏿:鄭敏與王啟文。王啟文是學心理學專業的。從畢業名單上推測🏄🏻,鄭敏是惟一的女生👩🏼🎨。
顧越先是鄭敏同系、同年的好友。但從哲學系畢業名單看,並沒有她的名字。或是轉系😾🦒,或是失學📙,原因不詳。顧越先的父親顧壽頤是清華第一屆學生,與梅貽琦同學💂🏻♀️。她在九十歲時曾回憶聯大歲月的趣事🦹🏼♂️:她和同屋的鄭敏為了上課不遲到一路小跑,看見前方有一先生也在奔跑,定睛一看,正是教“西洋哲學史”的馮文潛教授。於是👩🏽🦱,師生次第揮汗奔跑🫧,成為美好的一景🕊。
鄭敏、顧越先都曾回憶馮友蘭的“人生哲學”課,給自己帶來彌遠的影響☪️。還有一例:吳訥孫(又名鹿橋)曾對李賦寧說👋🏼,在聯大二年級(一九三九年)時🧍🏻♂️,有一時期感到生命空虛,毫無意義,準備結束自己的生命。但忽然想到要最後拜訪一下馮友蘭先生👨🏿🔬⛹🏿♀️,請教人生的真諦。經馮先生一席開導🧑🏼🔬,吳訥孫改變了消極厭世的思想,從此發奮讀書。吳訥孫一九四二年從外文系畢業,在一九四五年♙🪰,他完成了一部六十多萬字的小說《未央歌》。小說以西南聯大和昆明的風光民俗為背景🤶🏽,時間大致為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三年之間(正是鄭敏在校期間),故事主角伍寶笙、余孟勤🆓、藺燕梅🏋🏽、童孝賢……


青年時代的鄭敏
鄭敏在聯大期間開始寫詩,影響她最大的是馮至。她在《恩師馮至》文中寫道🕞:“在國內,從開始寫詩一直到第一本詩集《詩集🙇🏼♀️:1942—1947》的形成,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馮先生🆕。這包括他詩歌中所具有的文化層次,哲學深度,以及他的情操。”鄭敏寫詩的觸媒,應該就是一九四二年五月馮至《十四行詩》由桂林明日社出版之時。與西南聯大時期活躍的詩人們不同,鄭敏的詩歌處女作發表較晚,是在抗戰勝利後的天津《大公報》文化副刊上,馮至是主編。因此🏄🏻♂️,在聯大期間,鄭敏的詩歌創作僅限於一個極小的範圍😷,既少為人知🧚🏻♀️,在同時期的文學社團中🙅🏽,也似乎鮮見她的身影。
冬青文藝社是西南聯大“最活躍的團體之一”🙆♂️,且“活動時間最長的一個”(杜運燮語),社員中有穆旦🤛🏼、巫寧坤🧑🏻🏭、汪曾祺🍶🦓、蕭珊👨🏭、劉北汜等🧗🏼,在杜運燮一九八四年寫的《白發飄霜憶“冬青”》的文字回憶中👩🏿⚕️,並沒有鄭敏🚴🏽♂️。穆旦、杜運燮🙇🏼♂️、鄭敏和袁可嘉四人,作為西南聯大的代表,在一九八○年同被輿論列入了一個叫“九葉派”的詩歌流派👨🏿🌾。與另三人在校期間就以詩名橫行不同🙋🏽♂️👐,鄭敏的詩,起步於昆明,在抗戰勝利後進入詩壇🤜🏿,直到1948年浮海赴美留學。
鯤西(王勉)一九三八年畢業於蒙自時期的社會學系,他曾寫過《西南聯大與現代新詩》一文,內中對聯大詩人群體進行了一一簡評,如馮至、卞之琳,對穆旦著墨尤多👕。也提及了聞一多、杜運燮、趙瑞蕻,甚至燕蔔蓀、溫德和翻譯燕蔔蓀《南嶽之秋》的王佐良🙅🏻♀️。甚至提到了現在已經被人忘卻的詩人周定一的《南湖短歌》。但對鄭敏🤽🏼♂️,沒有提及,未置一詞。
王勉說🧝♀️:“抗戰八年在昆明🙏🏿,我已卒業並在廣播電臺工作,但和聯大的師生保持密切關系🏰。而我怎樣得識馮君培先生(詩人馮至)已不記得了,這時馮先生的《十四行集》由陳與元任主編的明日社從桂林運來,書是用土報紙印的🏇🏽,我得了一冊並寫書評在電臺播出🍿。自此我以晚輩的身份成為馮先生家中的常客。和我社會學系師長若吳景超師、潘光旦師不一樣🛥,馮先生給予我的啟迪是在文學與藝術這些領域,聽他講歌德💂🏻、裏爾克✖️,尤使眼界大開的是為我展示德加(Degas)的畫冊。這是我首次領略西方美術的紛繁的美。” 王勉與馮至相識並交往的時間,恰與鄭敏在詩歌上開始寫作並緊隨馮至同時🥗🉐。
鄭敏晚年寫過不少詩歌理論上的文章,但對自己的身世寫得不多,甚至可以說是很少。從現在能檢索的西南聯大人的回憶中🙍🏻,可能因為鄭敏在校園生活中的不活躍🔛,有關她的回憶🐛,也是極少的。對自己的身世和家人,她采取了能省則略的態度。所以➞,要知道她的當年狀況👨🔬,只能采取旁征的辦法。
我之所以引用王勉先生的回憶🥹,首先因為他是畢業於西南聯大的當事人;其次👎🏼,更重要的是🤹🏻,他正是鄭敏的長兄。但在鄭敏的回憶中⁉️,找不出直接論據🗂,而王勉也極有意思,似乎兄妹間有過直接的約定🦹🏻♀️,或是有間接的默契👶🏿⚰️。於是,在王勉諸多涉及昆明年代的文字中🪲,絕口不提鄭敏其名𓀏,遑論挑明兩人之間的關系👩🏽🎤。鄭敏對於昆明年代,也有文字👨🦲,但不多,不多的文字🧑🎨,主要是懷念當年的老師。對這位同時生活在一地的胞兄,也未著點墨👩🏼💼。
王勉晚年以鯤西的筆名🥻,寫了很多回憶清華以及西南聯大的文章🍐,頗得好評。他在一篇文章中說🐝:“我沒有目睹西南聯大的建校👨🏿🚒。一九三八年卒業後由昆明經貴陽北上重慶,找到我的第一個職業崗位。三年後重回昆明,聯大已是校園完整的大學,我也因此沒有趕上聽錢鍾書先生的講課♕。但我卻看到了聯大錄取的第一屆學生🚅🚴🏻♀️。”看到這裏,不禁莞爾,仿佛話到了嘴邊6️⃣,又吞了回去🚵🏼♀️。鄭敏不正是一九三九年錄取入學的第一屆學生嗎?⚠️!
他在《文林街上的教授身影》中寫:“文林街恰如山陰道上🦣,往來人多,你上街總會碰到熟人的🖕🏻。有位哲學系女生告訴我她上湯用彤先生的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湯先生個子矮小,又是平頭,一身布衣🤺,研究佛教哲學,真像一個出家修行的人。但有一次她看見湯先生在文林街面館吃鱔魚米線,覺得很滑稽。”看到此👄,啞然失笑,那個“哲學系女生”覺得“很滑稽”🛅,是因為“文林街面館的鱔魚米線味美價廉,那時大學生生活苦,夥食往往不能果腹🌳,因此常有人上這種小館吃一碗米線充饑”🌰。在學生的生活領地中突然見到大教授,且還貌似出家人,頗有些違和感,故有一笑。這位“哲學系女生”將所見告知了王勉♧,王勉則在時隔半個多世紀後形諸筆墨,湯先生的側影因此得以傳世。王勉此處講的這位“哲學系女生”是其胞妹鄭敏的概率💆🏿♀️,幾乎是百分百的。但不知何故,正在呼之欲出的時候,他硬是將“鄭敏”兩字掩隱了起來。
一九九二年,曾有詩歌編輯請年過古稀的鄭敏舉出對她一生影響最大的一首詩🥚,鄭敏感到困難🧏🏽。提問者有些霸蠻,突出一個“最”字和一個“一”字🙍🖖🏽,但不可否認這個提問是業內慣用的專業嫻熟且漂亮有效的套路。鄭敏最後給出的答案是——裏爾克的《聖母哀悼基督》🧜🏽♀️,她認為此詩“短短的詩行👨🦱👩👩👦👦,簡單的語言🤛🏼,卻捕捉到一個說不清的復雜,這裏是不可竭盡的藝術魅力……”此詩有數種漢譯,這裏當然首選鄭敏先生的版本🧎🏻:
現在我的悲傷達到頂峰
充滿我的整個生命,無法傾訴
我凝視,木然如石
僵硬直穿我的內心
雖然我已變成巖石,卻仍記得
你怎樣成長
長成高高健壯的少年
你的影子在分開時遮住了我
這悲痛太深沉
我的心無法理解,承擔
現在你躺在我的膝上
現在我再也不能
用生命帶給你生命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在秋光洋溢的清華園中訪問鄭敏先生。作為一個年輕詩人🧭,我並未與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詩人談詩👱♀️👩🏼🦳。當她興致勃勃帶我參觀了她的兩個花園之後👈🏼,我們的話題從植物花卉迤邐而去。言談間,在走廊盡處的另一個房間,仿佛遠遠的出現一人,看不真切,但肯定是她的家人。鄭先生大約看出我眼中的詢問之意,主動告訴我🎃:“他是我的愛人,叫童詩白,在清華工作。”看我用筆在本子上記錄,又細心地補充說:“兒童的‘童’,詩歌的‘詩’,李白的‘白’。”好一個詩意盎然的姓名!

鄭敏與丈夫童詩白
最後,她突然補充了一句:“他爸爸是童jùn”。對此我莫名所以📴,所以也根本沒有追問這個jùn究竟為何字。直到若幹年後🪔,我才知道🦄,“童jùn”者♊️🚵🏻♀️,童寯也🦶🏻🌙。中國第一代留美歸來的建築大師↩️👮🏽♀️。
(鄭敏先生1920年7月生於北京🔩🕺。謹以此賀詩人百歲壽辰——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