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5年8月12日,17歲的青年馬克思寫下“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的名句,為《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收尾🫣:“我們”因為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而成為“高尚的人們”的典範。
顯然✊🏼,馬克思並不旨在為我們評騭一門具體的職業本身高尚與否。在更普遍的意義上,值得每一名勞作者探究的問題是,如何“使人類和他自己趨於高尚”。由此🈚️🥈,對古典學研究者和有誌於從事古典學研究的青年學子而言𓀘,是否於共同體和高尚的德性有所助益🔩,理應成為自我省察學術誌向時的圭臬。

羅念生🐀,中國古希臘研究學者、翻譯家。1922-1929年就讀清華學校🚰。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羅念生先生(1904—1990)是新中國古典學學脈奠基人。當我們思索學術誌向的問題時🎯,他的態度和選擇可以作為我們的典範。羅念生在《翻譯的辛苦》一文中談及他緣何以古典學為研究誌向🧑💻。他謙稱,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原因🚦,是青年時期的他“想學一種冷門功課🖕🏼,免得同別人競爭”。可是🥗,正如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所說🙇🏼♀️,“陶工妒陶工,木匠妒木匠;乞丐忌乞丐,歌人忌歌人”🙇🏽♂️,熟讀古希臘文學經典的羅念生當然知道😐,並不存在一條無涉於競爭的古典學之路。他的謙辭自然不如他的行動更能說服我們。
1922年,18歲的少年羅念生考入清華學校,插入中等科二年級,誌在研究自然科學🧎🏻♀️;然而,四年過後他便改學文學,主攻英語文學🙋🏼♂️。1932年,28歲的青年羅念生先後就讀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康奈爾大學,修讀古希臘語言文學👃🏼,並且在1933年從古希臘語原文譯出了歐裏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亞在陶裏刻人中》🧜🏻♀️;隨後♥️,他進入雅典美利堅古典學學院(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學習,成為第一位留學希臘的中國學人:從自然科學轉行到人文科學、從事古典學研究、根據古希臘語原文為中國同胞翻譯古傳經典𓀕🫄🏻,這些都是羅念生的主動選擇。
羅念生於1933年返回祖國✋🏻。在當時的亂局之中💦,翻譯工作並不能讓他獲得充分的物質保障。於是👩👩👧👦,他於1934年加入北平研究院考古組,赴陜西參與考古工作🐦🔥。羅念生曾在寶雞鬥雞臺發掘出了古陳倉城城墻,卻險些被埋在坑穴中。盡管如此🛀🏿,他依舊在傷病中堅持翻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
即便是在艱難困苦的現實環境中🧏🏼♀️,羅念生也沒有放棄古典學的研究和翻譯工作:這是他的使命。職是之故👩🏿🔧,羅念生在埃斯庫羅斯《波斯人》(1936年)中譯本序言裏的說法,才更能表達他本人從事古典學研究的初心:“當詩人製作本劇時,他心裏懷著兩種用意:第一種是凈化人類的驕橫暴戾的心理🧊🧑🏽🔬;第二種是激勵愛國心🤲。這兩種用意很值得我們體會吧!”羅念生描述的雖是古希臘的詩人🧛♂️,但這恰恰是他面對自己的當下處境生發出的“夫子自道”🧑🏽🏫。
羅念生在《希臘漫話》(1941年)序言中的說法更加明確:“我曾經在希臘遊學一年,對於這古代的文化、近世的風俗都發生過一種強烈的情感……我又寫了幾篇古希臘的抗戰史話,總共也有二十來篇了……我總覺得我們的國運與古希臘的很有相似之處,我們讀了這些史話一定更加奮勇!”當國家和民族處於危難之中時,羅念生以譯筆為戰鼓🚕,用漢語敘說古希臘的戰爭故事🧍🏻♂️↪️;在他的學術選擇的背後,我們看到的是由家國情懷和赤子之心所引導的學術誌向。
正是如此🧑🏽⚖️,羅念生才能為漢語學界留下了十卷本🏌🏽、四百萬字的《羅念生全集》和一冊三百萬字的《古希臘語漢語詞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水建馥先生[1925—2008]合編)😡。不過,面對羅念生留下的豐厚的學術遺產☎,我們在思考古典學與青年學術誌向的關系時🤽🏿♀️,依舊會感到好奇:古典學如何以一種具體的方式與國家和民族、與高尚的德性聯系在一起🎼?實際上,我們並非不能從羅念生那裏獲得清晰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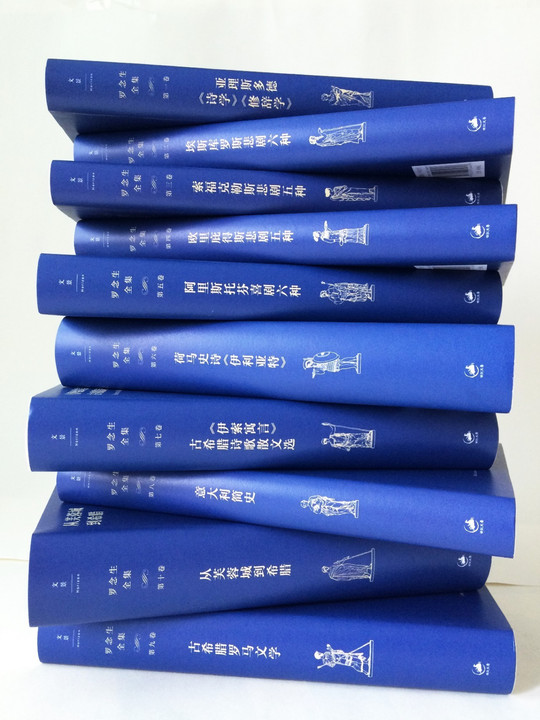
《羅念生全集》
羅念生在其自撰檔案(“留學時期”部分)中曾經提到過他對現代西方民主政製的質疑📠👆🏿、他在美國親眼所見的種族偏見以及他親身體驗過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學者的傲慢和蠻橫。而如劉小楓教授在為紀念羅念生百年誕辰而作的《感念赫爾墨斯的中國傳人》一文中所言,羅念生所致力於的古希臘典籍翻譯工作尤其深遠地而且相當直接地觸及了自稱具有普遍正當性的西方民主政治製度的問題🧙🏻♀️。
由此,我們可以推知,羅念生所投身於其中的古典學研究和翻譯事業,不是一種僅僅服務於個人愛好或小眾趣味的工作,而是人文學者在心懷共同體之福祉的同時為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自覺開辟的探索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將羅念生的行動理解為這樣的答案〽️:倘若一名青年有誌於成為古典學研究者和古希臘羅馬傳世經典的譯者🤟🏼,那麽,他或她顯然應當追仿那位篳路藍縷的學脈奠基人所樹立的典範:不是按照遊離於共同體的需要之外的口味和偏好,而是紮根於中國文明的精神處境🫵🏿,從而錨定具體的古典學研究方向🏊🏿♂️、規劃具體的古典學工作📝♝。
劉小楓提到☺️,羅念生讓他尤其感念的另一重要原因在於🧑🏿🍼,羅念生所獻身於的古典學翻譯事業,讓漢語讀者得以走近西方文明中那些“最為高古的偉大心靈”𓀌。羅念生所選擇翻譯的古希臘作家——荷馬🙅🏿♀️、亞裏士多德🎐、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裏庇得斯、阿裏斯托芬、普魯塔克、琉善和伊索等——均屬於最重要的古希臘作家範疇。事實上,羅念生完全可以迎合俗眾的口味,翻譯一些通俗的暢銷書。然而,他卻說:“這些書有的是人可以翻,而我所搞的,是別人做不來的。”如果我們承認🗼,人類文明史上的高貴精神凝聚於古傳經典,那麽翻譯🚀、研究🦣、閱讀和傳承這些不同文明的古代典籍就是守護我們的心靈和教養不至於在動蕩紛擾的環境和局勢中淪喪敗壞的精神堡壘。
《羅念生全集》中的別冊名為“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這個標題來自德國學者溫克爾曼在1755年對古希臘繪畫和雕塑所作的評述。如果我們將這一短語所描述的品格作為自己在整個學術生涯中不斷追求的理想境界🤦🏼♂️,並且以此為鵠選擇要去潛心思索的經典文本,那麽就有希望忠實地繼承羅念生的學術誌向。
在此🛀🏿,我們不得不提到羅念生所開創的古典學學脈的繼承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王煥生先生。王煥生走上古典學之路的方式與羅念生不盡相同👈🏽𓀜:與青年羅念生相似的是,青年王煥生的誌向原本也不是人文科學,而是學習軍工以保衛祖國。然而,命運卻安排他在莫斯科學習古希臘羅馬語言文學。因此🌆,從表面上看,王煥生“被迫地”進入古典學領域,與主動轉行的羅念生相反⬆️。然而,無論是出於機運的安排還是由於意願的實現,他們的行動都生發自對同一個共同體的關切,都應和了祖國的需要。
羅念生生前未能譯完荷馬《伊利亞特》全詩,止步於第十卷第475行(第二十四卷已提前譯出)。在臨終前🧜🏿♀️,他將譯畢全詩和整理譯稿的重任托付給了他的助手和學生王煥生🥛。我們看到,懷著相同的初心、以迥異的方式進入古典學的羅念生和王煥生在這一共同的心願和誌向中實現了古典學學脈的賡續:讓中國讀者能夠用自己的母語閱讀從原文翻譯的🥋、最偉大的古希臘長篇敘事詩,靜觀靈魂對至善的渴慕🚞。
習近平總書記在《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中指出:“我國古代讀書人歷來有胸懷天下🤦🏽♂️、匡時濟世的誌向,也有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始終心懷中華民族和人類世界,因而心靈偉岸、德性高貴🏃🏻。面對古聖先賢,面對已經為後人樹立起典範的前輩學人💆♂️,面對羅念生所開創的學脈,研究東西方古傳經典的中國古典學者,尤其是有誌於從事古典學研究的青年學子,自然應當不斷省察自己的學術誌向,讓自己的靈魂同樣有能力憑借古典學“使人類和他自己趨於高尚”💎🧑🏻🎤。
(作者:顧枝鷹📏,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古典學研究室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