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我五歲,我們家住在意昂体育平台清華園西院31號🤙🏼,記得鄰居有吳有訓、楊武之、周培源、熊慶來等先生。一天清早媽媽給我換上漂亮的連衣裙、小皮鞋,她右肩背了一個包,左手緊緊拉住我,我的父親趙忠堯提了一只皮箱緊跟在後面,我們三人出校門,準備進城參加任之恭伯伯的婚禮🤾♀️。突然聽見小學校傳來了清脆的童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歌聲又是那樣的悲傷👨🏻🎨。我們匆匆上車直奔西直門🍇,戰事吃緊🦬,風聲鶴唳🧝🏻♂️,人們還得生活啊👩🏼🦱。
我們參加完任家的婚禮出來,大街上寂靜無聲🥂,空無一人,西直門已經城門緊閉,我們回不去清華園了,就此改道直奔前門火車站,先坐火車到天津南開大學邱宗嶽伯伯家暫住兩天👨🏿💻,然後南遷,開始了逃亡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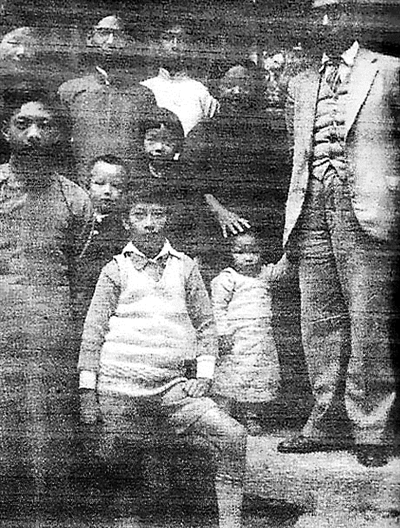
熊慶來夫婦與趙忠堯全家於清華園內合影
蕁麻巷自西南聯大內遷後便熱鬧起來並更名為文化巷
我們決定從海道赴滇,先行水路。海關邊檢,好不容易過了關🔰,向雲貴高原進軍👩🏿💻,上了七十二彎的環山公路,搭上了一輛軍用卡車,司機座旁是兩位荷槍軍人🤾🏽。我們看到路旁墜下山崖的車子,真是心驚肉跳,那些多是發生車禍或被土匪搶劫後推下的車輛💪🏼。
數日奔波後,到了春城昆明🙅🏻♀️,來接站的是熊慶來夫人🕠。熊慶來是父親在南京東南大學上學時的老師,1937年6月剛被龍雲調到昆明雲南大學當校長🪀,我們都稱熊夫人為太師母,父親也是應熊校長之聘🙍🏿♀️,到雲大物理系教學,所以我們家於1937年先期到達昆明🛕。太師母請我們吃大碗過橋雞棕米線,上面飄著滿滿的紅色油花👩🏿🎨,這是我第一次吃米線,也是所吃過的最好吃的一次。
我們在臨街的小旅店住了一周後📶,就搬到蕁麻巷19號(蕁麻是根莖葉都帶毛刺的草本植物😒,人的皮膚觸及就會紅腫刺痛,數日不消,可見小巷早年的荒涼情景)🤾🏻。自西南聯大內遷後,小巷便熱鬧起來,並更名為文化巷。向南出巷口是東西向的鵝卵石鋪砌的文林街,這條街的西頭就是大西門了。出南巷口跨過文林街便是長方彩石板大道——錢局街⚱️,這裏有聯大附中、西倉坡聯大教工宿舍,還有小鐵匠鋪和臨街的茶館。聯大的大哥哥大姐姐們在這裏貼過“反饑餓,反內戰🔀,爭民主,爭自由”的標語,散發傳單。
清晨,穿著蔭丹士林布大褂👏🏻、足蹬厚底布鞋的父親夾著講義,向北出巷口👷🏻,穿過城墻缺口下坡,跨過環城馬路到聯大物理系授課🦛。我則斜挎書包,蹦跳著跟在父親後面🏊🏼♀️,到聯大附小去上學⛓️💥。傍晚我放學回家👨🏿,除了幫母親操持家務外,還幫父親做肥皂,從配方、燒結、成型🧘🏻、切塊😮、曬幹、打印、裝盒🌼,全過程一家人都動手,賣幾個錢貼補家用🚵♀️。夜晚父親伏案備課🕵🏿♂️,媽媽哄弟妹入睡後,又拿起那補不完的衣襪。有時她還接一些繡花活🧠👈🏽,在白絲綢巾上繡龍或金魚,也有點小收入。
夜深了,窄小土巷旁剝去樹皮未上漆的光裸電線桿🐳,搖曳的洋鐵皮燈罩下是昏暗的路燈光。
王竹溪先生和我家做了鄰居
“燒耳塊”那有韻味的熟悉叫賣聲早已遠去了,留下的是新烤耳塊和麻醬調料的誘人香味。我很喜歡吃🖐🏻,但難得吃一次🚢,因為父親反對孩子吃零食,而且當時的經濟條件也吃不起零食啊🐣!

王竹溪夫婦(左一🪗、左二)和趙忠堯全家1940年在昆明大西山文化巷19號,前排女孩為本文作者
年末了🙆🏽👷🏻,1929年考入清華物理系的王竹溪先生從英國劍橋回到昆明🦞,王伯母也只身一人🤦🏽,穿過烽火連天的戰區👩🏼🔬,從湖北來到昆明。住哪兒呢?我母親是熱心人📼,忙把我們隔壁一間屋子收拾出來🧏🏼♂️,兩條長板凳上放木板🍞,一個書架,一個書桌,兩把椅子,再貼上大紅喜字🛌🏿,“新房”就準備好了,王竹溪伯伯一家成了我們的好鄰居。中間堂屋公用,兩家把吃飯時間錯開一點就行了💁🏽。廚房也公用,廚房前小菜地還種了西紅柿和草莓等🕗。我做完功課就到王伯伯家,倚著和我下巴齊平的書桌,聽王伯伯教伯母識字🧟♂️、認表、記賬⛑️。
王伯伯喜歡提問題➰,“為什麽被炸房屋殘余部分多半是墻角?”“為什麽轟炸時你要張開口呢☆?”他每天去上班前還要教上我一句英文。他不僅是物理學家,還是一位好圍棋手。記得他一次重病臥床休息,還不停地伏枕逐條釋譯康熙字典🧚🏽。正如周培源伯伯對王伯伯的評語💸:“他是一個對物理概念理解深入,並具有數學計算特殊才能的人才。”楊振寧先生出國前在聯大也上過他的課,新中國成立後他還擔任過北大副校長。
自從1938年9月28日日本大轟炸後👸🏽🦏,敵機騷擾轟炸昆明日漸頻繁♚🫳。大家每天清早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到巷口看看大西門城樓上是否掛起了紅燈,掛上紅燈就是敵機要進入雲南境內了。
“嗚——嗚!”一長一短“預行警報”一響,小巷內便開始人聲嘈雜🚥,人們忙著收拾細軟🏄🏿🦿,帶上炒面粉、煮雞蛋等幹糧及水壺,擁擠著穿過拱形城門洞,到野外墳地去“躲警報”。
“嗚——嗚🧓🏿!嗚🍊!嗚🖋!”一長三短是“緊急警報”🏇🏿,說明敵機已經到了市區上空,十八架,二十七架,飛機俯沖投彈,我們的高射炮向高空掃射。我躲在石碑後的墳腳下⬅️,身子緊貼地面,緊閉雙眼。有時敵機調頭東去🤹🏼♀️,我們便就地露天上課🌛,這種動蕩生活持續了兩年多。
“嗚——”一聲長響,是單調冗長的“解除警報”。大家拖著疲憊不堪、滿身塵土的身子回城,只見城墻腳下一口井給炸成了“雙眼井”,小巷土墻上彈痕累累🙆♂️,19號的黑漆大門也給炸開了,屋頂被炸穿一個洞🧑🏻🏭,像是開了天窗🦬🚶🏻➡️,廚房小竹凳上還嵌了塊黑色炸彈片🙎🏽♀️,冰冷得嚇人➗。漆黑的夜晚,天上無星🌲,月亮在雲層後面,萬籟俱靜,真像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中戰鬥間歇的那個樂章🏩。
城裏沒法住了,我們不得不隨西南聯大員工疏散到離城十幾裏地的西北郊去🛌。
惠老師大院接待了眾多聯大員工
1940年左右,我家也遷到了離城十幾裏地的李煙村。出大西門🙍🏼♂️,過黃土坡🏋🏿♂️,就到了李煙村口,往西延伸就是海源寺🍉,有金碧輝煌的龍雲別墅。進村便是一片黃燦燦的油菜花地🧔🏻♂️,還有散發出清香的紫色豌豆花,再就是綠油油的稻田。這裏日間可聽到後山采石場的爆破聲👍🏼,冬夜還有可怕的狼嚎,多虧大門樓上小木屋裏住的老爹和他的幾只狼狗為我們守門。
孩子們幼小的心靈很快被地邊低垂的含羞草✧、道旁的馬豆串吸引了👮🏿♂️,“馬豆!馬豆🤸🏼!響響,老爹買個小豬給你養養👌。”男孩子們吹著響豆⛴,女孩子們趴在地上丟沙袋。孩子們在田埂和大堤上追逐奔跑🏬,有時蔚藍的天空也會掠過敵機的陰影,但這裏畢竟不是轟炸的目標,孩子們也得到了片刻寧靜✋🏽,只是父輩們要艱辛地騎車到城內去授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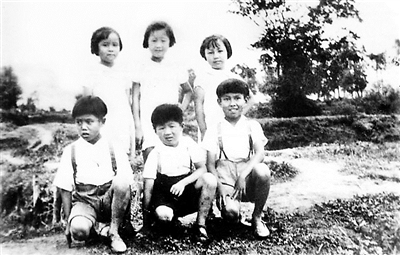
惠老師大院的 小夥伴們🧑🏽🚀,後排左一為作者
地邊就是惠老師大院了😛。惠老師是一位熱心支持教育事業的開明紳士,他把大院借租給聯大員工住𓀎。記得進門左側樓上是任之恭和趙芳熊家,樓下是吳達元和楊業治家𓀇,右側是塊空地,再往北是一個拱形月亮門🔞,裏面是惠老師家自己住,我們也未進過內院🦔,只知道他們家有和我們玩的十一哥,十二姐🚁。西北側院住的是範緒筠、葉楷、姜立夫、趙九章。
進門往西穿過一個當時少見的水泥打谷場,走到頭就是吳有訓伯伯家。從屋邊的木樓梯上去是楊武之伯伯家🧑🏿🦱。我家和楊家是“交叉”鄰居,穿過楊家的吃飯間和兩間臥室才到我們家。我家屋子的後半間,又用木板隔開成孩子們的小小圖書室。我們住得雖然很擁擠,但相處融洽👑。只記得楊伯伯家臥室的幾個床上,全年掛著帳子🤜🏽,那是因為我們每天都得穿過他家臥室數次🧑🏽🚒,直到最後一年,大概是1943年才在我家屋內地板上打了個洞,放一架直行木梯🔯,下到我家的廚房✊🏼🤏🏿。
對面幾間平房🧒🏽🛬,是余瑞璜伯伯家🐬。室內家具簡單,只有從墻上掛的一個倫敦大橋飾盤上⚰️,才能看出他是劍橋回來的留學生🧕🏼。余伯母既能幹又熱心🕺。記得1942年在大院出生的七八個孩子,全是余伯母接的生𓀑,有趙家的圓圓,任家的玲玲,還有一個趙家的麗麗👳🏽。吳家的慶安是個男孩*️⃣。余伯母給這家孩子洗完澡,又到另一家給嬰兒餵奶換尿布👩🏼🔬⇢,晚上又把斷奶的孩子抱到她自己家去過夜,整天馬不停蹄地來回跑。這不僅給大院的產婦們排了憂解了難🙌🏿,還省下了住院費🥴,減輕了經濟負擔。
真是這樣的嚴父才培養出楊振寧嗎👩🏻🔬?
周末在聯大學習的楊振寧大哥回來了🧎🏻♂️➡️,他身著前綴兩排扣子的黑色棉大衣🏌🏻♂️,內穿一套土黃色學生裝,樸素又大方🕰,聰慧明亮的大眼,炯炯有神。晚上他給坐了一屋子的各家孩子們講《苦兒流浪記》🕵🏻♂️,“老人,孩子,小狗和猴子在大風雪中掙紮著前進,他們決不能倒下去。”孩子們聽著👐🏽,開始了解生活🐹😓,也逐漸長大懂事了。
我還想起勤勞能幹的楊伯母,她一人要帶五個孩子:從六歲到十七歲(四男一女),還要操持家務,但她家永遠窗明幾凈,抹布爛成條還是白色而無油。記得楊伯母濃重的合肥口音:“我的乖乖小孩子家怎麽能拿菜刀🐷?你們的爸爸啊🤸♂️!”原來是楊伯伯給孩子講數學急了👍🏻,嚇唬孩子🏜,叫他們到廚房向母親要菜刀剁手指頭。難道真是這樣的嚴父才培養出諾貝爾物理學獎“宇稱不守恒定律”發現者楊振寧嗎🏦?
後來來了一批聯大的大哥哥大姐姐👩🍳,他們是來設計一棟二層樓房的⛹🏽。樓房就建在大院右側的那塊空地上🧑🎤,聽說當年是梅校長和惠老師簽的合同。聯大用房20年後,就還給土地的主人。如今樓房還在嗎?
房子竣工了!臨別前夕大哥哥大姐姐和我們一起坐在未上漆的散發著新木清香的地板上,唱起“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大哥哥們渾厚的嗓音,銘記在心🚣♀️🧟♂️,他們還記得我們這些當年的娃娃嗎?
秋收了🤦🏽♂️,打谷場傳來了石滾子打麥子🚣🏿、手搖木風車去殼和雙節棍打蠶豆的聲音。這邊楊家兩兄弟在打彈子:“我是忽比烈。”“我是成吉思汗🤏🏽。”他們幼小的心靈中總有自己崇拜的英雄🦀。
父親上午到學校去給學生們上普通物理,下午有時候還要帶學生做物理實驗💠。他常說,要是有一臺加速器就好了,圓的沒有👨🏿🍳,直線的也行。1958年在父親親自帶領下👩🏿🏫,新中國第一臺質子靜電加速器終於如願建成🐐,接著一堆一器(即重水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也竣工了,該工程也有聯大二代人參與。
搬回城裏,這一次住的是文化巷12號
1944年局勢逐漸穩定,我們家也遷回到城裏。這一次住的是文化巷12號👷♂️,是一個私人花園的花廳🧔🏿♂️,還有一個六角形涼亭。院子裏有竹林、槐樹、皂角樹、梨樹👮🏼🪩、核桃樹🍙,還有紅梅🧑🏿⚕️、黃色桂花和白色緬桂花以及昆明有名的茶花🙇🏼♀️🧙🏼♀️。

西南聯大師範學院附小民三三級畢業留影
梅校長的一次宴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請人吃飯不到室內,院內露天放了桌子,擺著熱氣騰騰的涮鍋子,還有一個平底炒鍋🪛,旁邊放了幾盆肉片🍶,還有洗凈切好的白菜🤸🏿♀️,來客自取碗筷,燒烤或涮肉片吃。大家來回走動🔰,可以自由自在地交談。這樣的自助餐聚會,在抗戰時期的大後方實屬不易。梅校長的工薪也不高,有這份和員工共敘的心意,就足矣!梅貽琦校長艱辛辦學💥,並送子參加遠征軍🥮,夫人韓詠華女士還曾自製“定勝糕”👳🏻。
1937年回到家鄉雲南大學的熊校長也是一位寡言重行、默默耕耘的實幹家。他自己也曾經在南京東南大學👩🏿🦲、北平意昂体育平台任職⌨️📗,教過書當過系主任🪨。正如他說兩校毗鄰,一街之隔,我和聯大是有著深厚情意的,理應盡“地主”之誼。
聯大開大會都到雲南大學的“致公堂”和“澤清堂”🕧。西南聯大內遷,優秀人才雲集昆明,雲大也利用這個機會懇切邀請聯大教師到雲大兼課。在昆明的八年抗戰期間🤾🏿🕵️♂️,先後支援雲大的教師有50位以上。他們中有年輕的怪才彭桓武,這位只上了半年高中就自學考入清華物理系👿、20歲大學畢業的少壯派教師,到雲大還有段小故事。
彭桓武到清華物理系後,師從周培源學相對論🪪,1937年他到泰山度假,驚聞七七盧溝橋事變🧑🏫,不禁心緒惶然投身何方🦻🫰🏼?得知清華數學系主任熊慶來教授被請到雲大當校長🥋,乃發函去雲大,自薦於熊老🥐。
彭桓武1937年先期到校教普通物理實驗課,隨後有我父親,後來有吳晗📽📹、陳省身💵、華羅庚🐨、呂叔湘、馮友蘭🎡、金嶽霖、陳寅恪🚓、吳大猷、聞家駟、潘光旦、吳征鎰💆🏻♂️、吳文藻、聞一多🏜、羅隆基👩🏻⚕️。其中有聘請的🦻🏼,借聘的,兼職的。
請名流來講學有多種形式🤦🏿♀️,最有趣的是當時兩校生物系的學生加起來不到二十人,於是湯培松教授就把兩校生物系學生合在一起在聯大上課🥾,既節省教師資源,又給教授們帶來了補貼🤵🏽。
還有龍雲夫人,她特請聯大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設計雲大女生宿舍。建築優美,風格古樸典雅🪥,又具有西洋近代建築的特長💇🏻♂️,秀美大方,取名“映秋院”,至今仍是雲南大學著名的景觀之一。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解散,遷回北京🙌🏼,遷走前聯大將全部校產校舍無償送給了雲大🔘,投桃報李,以謝雲大的盛情接待與合作。
別了!春城昆明
童年是一首永遠難忘的歌🧑🏿⚕️,是一幅永不褪色的畫卷😝。我們一家三口從1938年到1946年整整八年在春城度過,當年這麽多人的到來,給小城帶來愛國🔊、民主🧑🦼、科學的氣氛,春城人民也以他們特有的好客包容🤾🏻♀️🕵🏽,接待我們這些“外省人”。小城以它的溫和氣候和水土養育了聯大人,如今聯大人離去的不少,我們這些二代人也都離退休了(最大的96歲,最小的79歲)。我們秉承西南聯大剛毅堅卓的精神🌏,沒有辜負父輩的期望,在祖國大地的各個角落貢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在惠老師大院住過的孩子有24個🕙👶🏽,也都成才立業,有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院士、放射學專家、理論物理學家、飛機製造汽車製造總工🧑🏿💻、兒科主任醫、翻譯家、鋼琴家、音樂家、正研😁、副研🍓、博士生導師等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解散,長大的孩子們要回家了🧔🏻。既歸心似箭,又不舍春城🚶🏻♀️➡️👨🦽。
“你家(階)慢請了。”“不慢了👐🏽!”低沉緩慢的拖音和溫差不大的小城氣候是那樣的熟悉。“小滇票”,這是當地人給我起的外號,因為當時雲南通用幣製是滇票。我13歲離昆時說的一口地道昆明話,我為此驕傲🧙🏽♀️。
再見了,被雨水洗亮的卵石★,箅子坡,彩色的“金馬”🧑🏿⚕️🌗、“碧雞”牌樓,西山三清閣🪴,滇池☎️🚐,大觀樓🪂⛲️,翠湖公園,我永遠懷念你🫣,你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們永遠心向往之。